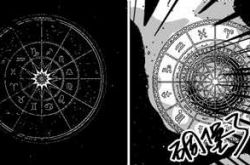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
——向埃特加.凯雷特致敬
现在,谁还会安安静静地坐到你对面听故事。听相声还差不多。但是相声已经成为奢侈品,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花费成百上千坐在德云社台下欣赏那群演员演绎人生百态的。于是,芸芸众生开始分化,一部分热衷于打机,王者荣耀和其它一些类似的手游开始占据一部分灵魂,东拉西扯的网络小说占据另一部分灵魂,剩下的一小撮自娱自乐地承袭传统,写起故事。
——不,我不读那些,我只要你给我讲个故事!他毫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命令道。
就在几分钟前,他刚刚从书里钻出来。是的,我没说错。先是一根手指,我还以为是我早餐剩下的那截烤肠,烤肠上还散发着墨香。然后是胳膊肘,脑袋。他吃力地钻出来,扬了扬手里的那把枪,清清嗓子,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命令我给他讲故事。但是我从没讲过故事。我患有轻度社交恐惧症,面对他人总会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好,尤其面对陌生人,尤其面对一个手持枪械的陌生人。转念一想,既然他是从书里钻出来的,那么手里的枪能有什么威力呢。他似乎窥视到我的想法,抬手就是一枪。子弹穿过凝滞的空气,打在窗户上,玻璃应声而碎。
——我不想使用暴力。显然你们中国人也不喜欢暴力,因为你们中国人胆小怕事,信奉中庸之道。不过如果你不讲故事,我就会使用暴力。在我们国家,人人相信暴力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能用一支航母舰队解决的事情,绝对不会用M16解决。而我手里恰恰有把柯尔特,所以我能够掌握话语权,你却不能,你手里没枪,没武器,你只有一张嘴,这张嘴我想让你张开你就要必须张开,我想让你闭上,你就必须闭上。所以现在我让你讲故事,你就要必须讲给我听。
说实话,我被他吓到了。我从没真正见到枪,虽然我安静地坐在家里喜欢看战争片,却从没见识过这样的阵仗。我嘴唇哆嗦,莫名地想到格雷塔.通贝里,琢磨他到底是哪国人,美国,德国,还是冰岛?我眼前这个男人也许是瑞典人,不也许是挪威人。他汉语说的很好,有几分布雷维克的模样,以至于我忘记了他是书里钻出来的。我家里有许多书。我喜欢那些作家,他们都是谙熟此道的大师,他们用灵魂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故事,他们如同一尊尊石像永存在我的记忆里。
——听我说,我试图跟他讲道理。
——你听我说,他再次扣上扳机,嘟嘟囔囔打断我的话:不准婆婆妈妈,要么给老子讲故事,要么让这颗子弹在你脑袋里开花!
——好,好,我现在就讲。我已经别无选择,这家伙来真的,我却不能寄望街坊听到这边的声响前去报警:两个人坐在一个房间里,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
话音未落,他顿时怔住了,枪口歪了歪指向我的书橱。我以为自己的故事把他吓到了。然而不是。我听到了敲门声。
——去,看看是谁,他手里的枪口动了动,指向书橱:记着,不要耍花招,否则我会不客气。不管是谁,都把他打发走。
这真的很怪异。我的手指刚刚触及那部格林童话,一个穿着白色公主裙的黑皮肤女孩儿从书页间蹦了下来,就像一只虱子或跳蚤刚刚摆脱掉宿主。她说她是唐纳德.巴塞尔姆的女儿,她说她身上七颗痣。她双膝并拢双脚分开,双手扭扭捏捏地按住裙子下摆,做出梦露经典的姿势。她说她认识胡佛,也认识肯尼迪。她说只想问几个简短问题,芝加哥的空气是否比哈尔滨的空气更甜美,安大略的湖水是否比兴凯湖的湖水更清澈。我告诉她,我从没去过美国,对美国也不感兴趣。她却置若罔闻,粗暴地把我推到一边。
——他是谁?白雪公主指着站在客厅的男人问道。
——他是租房子的,我撒了个谎:他刚从俄罗斯来,住在勘察加,他是黑龙江大学的交流生,正想和我讨论几个关于汉语语法的问题。
——可是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她执拗道:你先回答我吧,我保证不用滤镜,也不断章取义。说着她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他也挨着她坐了下来,喉结上下翻滚,两眼不由自主地瞟向她凸凹有致的胸部。
——我没空。我不耐烦道。
——真的没空?她的手从裙子下摆挪开,亮出一把德林杰,另一只手还握着针管,乳白色的液体,那是洗衣液吗?我迷惑了。她却勃然大怒地挥舞着那把小巧的手枪,歇斯底里地嚷叫:为什么没空?因为我是应该吃西瓜的黑人,因为我不够礼貌,或者因为我不是哈泼.李?对这个假模假样挪威人,你有的是时间,对黑人,对一个祖先被贩卖到北美又不得不汗流浃背地摘棉花的黑人后代,你他妈的连一分钟都挤不出来!要知道,我的祖先有许多都是因为没完成摘棉花的任务被砍掉双手的,难道你也要让我砍掉你的双手?——行了,行了,别他妈的废话,别找借口,赶紧讲吧!
——讲什么?我紧张得要命,生怕这位黑珍珠一个疏忽将子弹射穿我的躯体。
——你说讲什么,别考验我的耐心,我这人性子急,快讲故事!
——对,对,快讲故事!挪威人帮着腔,亮出柯尔特指向我。
——从前有三个人坐在房间里,我清清嗓子,擦试下额头打汗,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缓缓讲道。
——不要讲,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他提醒道。
——对,对,快点讲,但是不要讲敲门声,她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却依旧附和道:给我们讲点别的,刺激点的,比如警察当街暴力执法,比如大屠杀,比如你们都想移民到欧美,甚至想要移民到印度和,巴西和菲律宾。
我停了下来,深吸一口气。与此同时,他俩死死盯住我。唉,这真是倒霉,专写色情的贾平凹和武侠专业户金庸肯定从没遇到过这种事,义愤填膺的丹尼尔.笛福也不曾遇到过。就在这时,突然又响起一阵敲门声。这俩人目露凶光,黑洞洞的枪口不约而同地指向我。我的手心攥出了汗。这真的不关我的事,我压根儿就没再说敲门声。
——去,不管是谁,都给老娘打发走!白雪公主命令道。
我踱到书橱前,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一个胖子从书页间滑落。他笑脸可掬地迎向我,询问我是不是慕非。
——或者,你就是殷锡奎,躲在帷幕后面的那家伙。我是信史,我过来给你送书的,一部美国史,书里还介绍了感恩节,介绍了信仰基督的力量。你应该信仰基督,全世界的人都应该信仰基督,否则就等于没有信仰。
——你也是来这里听故事的吧?挪威人不由分说地打断信史的话:快别装了,把枪拿出来吧。
——我没有枪,信史难为情地说着,从那部美国史中间抽出一把锋利的电锯:不过,要是他讲不好的话,我就立刻以捍卫自由的名义用这把德州电锯把他锯成两段!
他们三人坐在沙发上,信史坐在中间,挪威人坐在右边,白雪公主坐在左边,电风扇吹过一阵风将她的短裙吹起,露出臀部的一颗痣。她乳房还有一颗痣。显然,她在利用七颗痣来引诱我。于是我告诉他们,这样面对着死亡我什么都讲不出来。
——你们走吧,我实在讲不出。我惶恐不安地讲道。
——这个狗杂种要报警!
——你是怎么想的,我们是三岁的孩子吗?
——拜托,我们听完故事就走,短一点儿没关系,我们保证不伤害你的,我们只是想听故事。
于是,我清清嗓子,重新讲起故事。
——四个人坐在房间里,天气好热,他们好无聊,其中一个说想听故事,另一个也想听故事,接着是第三个。
——闭嘴!白雪公主吼道:这不是故事,这是现实。我们不想听真实发生的事情,我们要虚构的,我们需要要虚构中寻找真理!充分调动你的想象力,给我们讲一个刺激点的故事吧!
我点点头,再次重新讲故事。有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家里,他患有轻度社交恐惧症,他想写故事。虽然他并不擅长写故事。他怀念自己的童年时期,怀念母亲,渴望生活在大宋王朝般富足和平的时光里,而不是一个架空历史。对,我不喜欢那些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谎言。我瞥了眼梳着脏辫的白雪公主,她正举起针管将乳白色液体注射进腋下静脉,脖子向后一仰眼睛微闭,手里的枪垂了下去。我提心吊胆地盯向他们,轻声讲起那管误将洗衣液当做K粉的故事,讲起我看过的那部栽赃陷害的好莱坞大片,讲起虎门销烟,讲起我坐在家里平白无故地遭遇到闯入者。
——突然,我说。
——我早就警告过你,不许说敲门!挪威人恶狠狠地说。
——可是没有敲门声就没有故事了。我固执己见道。
白雪公主哼哼哼唧唧,双眼流露出虚空,身子一软,那把德林杰无声无息地滑落到沙发下面。
——随他便吧,说着胖子站起身,不知什么时候脑袋扣上一顶白色安全帽。他捧着电锯,接上电源,温和道:让他讲吧,给他自由。你想说敲门声?那就说吧,只要你能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就行,反正这是你的最后一个故事。说着,他拽了下电锯上的绳子,屋子里回荡起嗡嗡的噪音。他叵测一笑朝我走来。

标签组:[挪威人]
上一篇:家暴和冷暴力哪个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