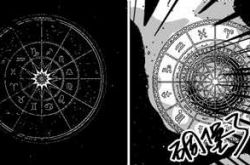发表自话题:蒋方舟日本
原标题:陈丹青:看蒋方舟的书,我很“生气”
前面的话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人的生日,我有些话想说:今天是易建联的生日,我们一起祝阿联生日快乐!”
喜欢蒋方舟、看过《圆桌派》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段子。
是的,今天是蒋方舟的生日,这个爱讲段子,喜欢自黑,自称过气网红的女作家,在《圆桌派》前两季中,给我们带来许多欢乐,也让我们听到了一个80后坦率而睿智的声音。
谨以下面这段视频,祝蒋方舟生日快乐!
除了这段视频,今天还想与你分享一篇蒋方舟和陈丹青对谈的文稿。
二O一六年,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之邀,蒋方舟在东京独居了一年。她用这一年的时间全然坦诚地审视自我、剖析自我,用日记的形式将自己完全暴露。
归国之后,她写了一本《东京一年》,用46则日记,记录了她这一年来在东京的生活,包括短篇小说、演讲和时评,驳杂不失纯粹。
陈丹青说:80后作者中,只有蒋方舟的书,他能从头到尾看完,但是看蒋方舟的书,也让他“生气”。
为何“生气”?接着往下看吧,文章很长,但很值。

到那陌生的地方去
对话:蒋方舟、陈丹青
本文转自微信公号:凤凰读书
部分图片来自蒋方舟微博
蒋方舟:谢谢。大家好!我是蒋方舟,这本书是关于我在东京一年所经历的成长,在发布会的一开始,我想做一个小的分享,主题叫做"到那陌生的地方去"。
世界上一直有两种旅行。一种旅行的本质是朝圣。怀着期望和虔敬走向预定的终点,收获满足或失落。
马可波罗的游记写下了梦幻般的扬州和汗八里,哥伦布念兹在兹的"印度"却是命运给他开的巨大玩笑。
这种朝圣式的旅行,即便最终旅行者没有得到预期中的答案,寻求本身往往就制造出有趣的记录。
另一种旅行的本质是隐遁:逃离自己所属的世界,踏入陌生的荒野。
30岁的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难以忍受婚姻窒息一样的压力,所以带着他的表妹一起在非洲进行了长达4周的徒步,他们徒步穿越过森林,这森林位于最贫穷的国家塞拉利昂与最失败的国家利比里亚之间,在旅行中,格林常忽然觉得自己处于长长的噩梦中。
27岁的我,在2016年在东京断断续续地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旅行,这旅行到底属于哪一种呢?当然是后者。
我厌倦了自己写作二十年以来的生活与身份,所以当一份陌生的邀约摆在我面前时,我毫不犹豫抓住了它。
我在东京的开始犹如一个游戏的开头:"一觉醒来,你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到达东京是晚上,被接到招待所,在黑暗中什么也不知道,像是卖给大山的女人。
第二天下午两点钟醒来,没有网络,手机不能用,没有地图,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也不知道一天该如何度过。
我出门步行了50米,在便利店买了一大瓶矿泉水,回到房间继续睡,睡到第二天下午两点钟。
后来我开始学习坐地铁,依着日本作家在东京留下的文艺地图去寻找,交朋友——多半是以喝酒的方式,才开启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生活。
在日本,我因为每天没有任何工作和安排,所以必须把每件事情都变得非常的漫长,才能填满一天的时光。
比如每次吃饭必须吃一两个小时才好,连一个咀嚼都长达30秒之久,要不然囫囵吞枣一天没事干了;每一幅画都看得非常认真,每一次观察都像长曝光,每一个念头都让它无限的延伸。
我把自己的每一个行为都变得无限延长,把每一个念头也无限的延长,因此获得了某一种近乎于严肃的体验。
上面提到格雷厄姆·格林的非洲旅行,其中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
因为非洲天气潮热,最好的表也会很快坏掉,格林带的六块表全部被侵蚀,最后只有一块表还顽强地走走停停,但它记的也不是真实的时间。
他本来计划用两周从一处到另一处,结果到他花了四周,从一个鬼地方到了另一个不知道是哪里的鬼地方。
而我在日本的游历其实也被取消了时间,没有社交或者是工作把日子分割开。我过的是完整且混沌的时间,社会分工所制造出的精准时刻被还原成模糊的流动。
在这种流动中,我可以认真地去观看和面对自己,而不用在社交场合去扮演自己,不用在公众关注下去扮演自己。
这回分享的题目叫做"到陌生的地方去",有两种意义,一个是地理上,一个是心理上。
某种意义上,地理上的远离才能实现心灵上的远离。

只有到另外一个地方,才发现原来自己心里存在原来不曾注意过和不曾发现过的角落。
如果你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就算你很想改变自己,也会发现生活的重力不断把你塑造成社会希望你成为的样子,以或温柔或残酷的规训把你拉回惯性的轨道。
而只有当你到达真正地理上遥远而陌生的地方,你才能发现自己心里还有这些没有被探索过的可能性。
说到这本书,读者若想从中找到我对日本国民性的观察和总结,那一定会失望。
一方面,那是因为一年的时间并不足以我对另一个民族做下狂妄的判断;另一方面,我发现人性大抵都是相同的,只会在不同的压力和容器中才会被塑成不同的样子。
在日本有两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它们甚至不能称之为"事情",更多的是像电影镜头一样的回放或者是情景。
其一是当临近开春的时候,樱花未开快开,非常美。
有一天,我在绕着皇居跑步时,忽然心里涌现出了一种类似于幸福的感觉,我觉得我处在一个非常安全、平静、丰腴且满足的社会,自己也过着一种非常平静和规律的生活,好像这样跑着就能够进入到一个正常的社会,只有樱花与酒、微醺的风和遥远而至的铃声。

我跑完步回住处看微博,发现华东师范大学的江绪林老师自杀,他的自杀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作为知识分子,自觉并不能对中国改变什么。
异邦生活的平静和国内知识分子真切的痛苦,在我心里造成了强烈的冲击。
还有一件事,去年7月,河北邢台发水灾。有一张小男孩死在海滩上的照片在社交网络上广为流传。
我在下午看了那张照片很难过,到了晚上,朋友约我去看花火大会,花火大会上很多小孩,坐在我前面的小女孩非常可爱,不断地对着天空绽放的灿烂大喊:"好漂亮!真美!"
我看着她扎着小辫的后脑勺,无忧也无惧的样子,我脑海里不断涌现的却是照片里那个与她年龄相仿的邢台小男孩的照片。
这两件事给我造成了一种感觉,我并不知道当时在日本所过的平静生活是幻觉,还是在国内的生活是幻觉。
电脑的或者是手机的屏幕,好像是一堵墙,把我与国内的生活隔开,我好像如果不盯着屏幕看,就能过一种完全规律、平和的生活,但我知道,屏幕那一头的生活才是自己的根底所在。
这一年,也是我远距离地观察我熟悉生活的土地,我并没有寻找到日本到底是怎样的国民,和我们有怎样的不同。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远方还是故乡,我看到的都是相似的人性,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制度的塑造下展现出的不同面貌。
格雷厄姆·格林四周的旅行,试图用脚去画下非洲的形状,但是当他踏遍非洲,却发现他画的并不是非洲,而是人心的形状。
对于我来说,我这一年的足迹遍布东京和日本大大小小的地方,但这一年结束,我发现我用自己的脚步画下的也并不是日本的疆界,而是形形色色的人心。

陈丹青:这本书我全部看完了,80后的作者我能看完他一本书的一个都没有,能看完一篇文章的也很少很少,只有蒋方舟上一本书,我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编者注:《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然后是《东京一年》,但是我昨天晚上看完你的书就开始生气,我今天坐在下边听你讲更生气,当然也可以说非常高兴。
高兴在哪儿?我算了一下,我比你大36岁,高兴在到你这一代终于不用再有我们这一代认的命运。
生气的是什么呢?我完全无法跟你沟通这种旅行,什么一个有目的的旅行、没目的的旅行一套一套的,我根本没有这样想过旅行。
为什么?因为47年前我的第一次旅行是完全没有目的的,是被迫的旅行,你知道,就是知青。
我现在经常听到谁双规了,我忽然想到自己很早就双规了,我们几百万上千万知青就是双规,规定地点你要到哪里去,或者内蒙古、黑龙江、江西、云南,都是穷的地方,上海、北京,一火车一火车拉过去,都是有分批、有计划的拉过去。
所以我从小就开始了被迫的旅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一去去了8年,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第一天去农村的样子,但你们都好意思把这经历说出来,我们这代人不好意思跟你们说这经历,听了之后烦死了,但这也是我们17岁时的亲身经历。
第二次旅行是有目的的旅行,到一个陌生地方去——29岁我到纽约去了,但我巴不得没有这样的旅行,太难受了。

所以看你里边写一个人洗衣,看着洗衣房的袜子在转。这无聊透顶了,而且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我是个男生,每个礼拜或者十来天要到洗衣馆去一趟,转,然后完里边扔钱,继续转,潮的话就把它拿出来晒掉或者怎么样。
但我生气还不是这个,我生气的是活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机构邀请我给我一个月2万块钱到一个国家,随便你干嘛。
我第一次妒忌阿城,他是被威尼斯邀请,也是作家,我也是称作作家,但没有一个人邀请我。
蒋方舟:觉得请不起。
陈丹青:从来没有过,他们都想用我,你到一个国家去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出差飞机票,当然我已经很高兴了,从来没有过公费留学和公费旅游,从来从来没有过,现在只有哪个地方邀请我到哪个地方去,其实不是像看画展、吃牛肉这些。
蒋方舟:花别人的钱跟花自己钱的区别。
陈丹青:倒不是这个区别,你提到歌德是37岁就溜到意大利待一年,希望把自己抛空了变成另外一个人,我已经生气了。
我一辈子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也想跑,也想有个地方去,躲开所有人,躲开社交,这一年把自己提升一下或者放松一下。
从来没有过,现在蒋方舟已经有了,你可以去日本,我倒现在都没有,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说。
蒋方舟:那就说看我的书有什么感想吧?
陈丹青:你很厉害,对什么事都能有观点,而且都很能清清楚楚说出来,我没有。别看我能说会道写文章,其实你很少在我的文章里看到我对一件事情会有像你这样的分析,我做不到,因为我们从小不是这种活法。
我们不是这么长大的,所以我很羡慕你能对每一件事情都有看法。
蒋方舟:职业习惯吧。我很好奇您17岁被迫的下乡“双规”,还有到纽约,当时有写下任何当时的日记吗?
陈丹青:有日记。但绝对不到可以发表的地步,我相信你写的时候是知道要发表的。
蒋方舟:但我其实也是节选,是自己删减过的。
陈丹青:但你是要发表的,我们写日记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会发表,我都找不到我的日记。在美国也写过一阵日记,但不打算发表。
当然我很喜欢你一些零零碎碎冒出来的句子,但这跟在座是无法分享的,而且每个人看书的习惯不一样,大家要看了以后再说。

1994年,木心与陈丹青,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门口石阶
所以我来的时候,我只能想起有两三个日记写得非常好,一个是你刚才讲的在黄道跑步,我完全没有这个能力,在跑步时居然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
因为最后发现这是中产阶级蛮优越的自我认可,这条路是我跑的,但其实它跟广场大妈没有区别的,这个见解很厉害。
说起来你不太相信,我其实是在学你,你是怎么看事物的?然后怎么能说出来?
蒋方舟:我是怎么看事物的?
陈丹青:我自以为对事物很有看法,但是看了你的书以后觉得,我不会这么看或者根本没想到这么看,这也是你们终于比我们这一代进步太多了。
蒋方舟:我觉得这不是进步,客观上还是因为我经历的很少,我说我的生活经历不是体力的经历,我觉得是因为我的经历很少,所以每件事都喜欢解剖出来。
陈丹青:我们经历太多,知识太少,你太早就有知识,但经历又太少,但知识还是有的,需要变得我这么多的经历,不是我来学会像你这样看事物。
蒋方舟:我觉得还有一点,可能因为我自身其实是一个没有什么情绪起伏的人,这是我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弱点,也可能是感情受创之后的后遗症,所以我无法感觉到人性的强度,就只能要么是用理性去分析。
要么是从书本里边去看到某种人性强弱的经验,但我本身是一个没有大哭大笑,大悲大喜经历的人,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也是被迫选择了只能用观点、看法、这看似是一种自我解剖,但其实是完全无痛的。

陈丹青:真会说话,一套一套的。自我解剖是不痛?
蒋方舟:您自我解剖痛吗?
陈丹青: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过自我解剖,但我有点会自嘲,但也就一句两句,不会像你这样一层一层挖进去,比方跑步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看脱衣舞。
我在美国的时候其实有三件事让我暗中大喜,一件可以公开讲——去看美术馆,我可以看到油画原作,这是我们那几代所有中国油画家做不到的事情。
还有两件我不好意思讲,一个可以吃鸡了,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吃一顿肉是非常难的,我们一年只有一张票一年吃一次鸡,据说美国鸡腿能随便买,当时太高兴了。
还有一个可以看色情画报了,1982年在中国休想看到一本花花公子,想都别想,但是我听说一到美国所有摊都有卖,男人都想看这些,我还没想到能看脱衣舞。后来我到了旧金山第3天,在旧金山的亲戚带我去看的。
说实话,根本不觉得这是自我剖析,没有什么痛不痛,就是很简单你想看,就想看一个女人脱光到底什么样子。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画过人体,对我没有那么的刺激,如果我在当知青的时候说,有个直升飞机把我拉到东京看完再送我回家,我马上会去,可是没有想到你一层层剖析后,说看脱衣舞是来自那张美国女作家的照片。
我也看过这张照片,但看那张照片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所以你的写作让我进入你的经验,也进入现在年轻人的经验,因为年轻人都会说他们的经验,但是说得好的非常少,你给我大量源源不断的经验。
原来这样的一个孩子,1989年生的,她活在世界上是这么看事情的,这是我觉得最高兴的地方。
再回到你刚才的问题,你们的文本经验、信息经验太多了,你是因为这张照片才想看脱衣舞,我什么都不用我就想要看脱衣舞。
小时候只要看到批判地方主义腐朽生活有“脱衣舞”这三个字出来,就会觉得世界上怎么有这样的事情?
我只是不敢相信有一天会看到,看到以后很失望,就像你说的,希望下一个再漂亮一点,结果都不太漂亮。
第三个我想讲的,你当中回国了一次。然后你在路边看到了杀人,把杀人写得这么感性、这么冷静,但我觉得一层一层写下去,非常有力量。
我是很爱写作,我要像你学习写得这么简单,你没有很冗长的议论和描述。我记得福尔斯写过看人杀头,非常简单,两行字没有了,我非常的失望。
但后来我发现这是有效果的,他知道写长了没有效果,写短才会有效果。你写那么短我非常佩服,如果我看到一个人被杀了就想注墨描写,但你没有。
蒋方舟:可以调解到几乎为零。
陈丹青:好像用不着调解,是天生的,女人看到血和男人看到血不一样,女人看到血比男人勇敢冷静多了,男人看到血一塌糊涂,我现在非常怕看到血。
我小时候亲手杀鸡、亲手杀蛇,但现在想起来跟野兽一样,连电视都不看。
蒋方舟:我觉得死亡这件事当然是不好的,但对于作家来说,能够近距离的看到死亡,其实是一个挺宝贵的财富。
陈丹青:三个人为了你看到杀死了。
我有一个观点,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被写出来等于没有发生,一点用没有,白死了,但真的被你写出来了。他们为了你这么几页纸都死掉了,死的人好像有30岁左右。
蒋方舟:死了两个,一个重伤。
陈丹青:你写他那儿躺的样子也特别好,一点特征都没有,而且是死亡让他没有特征,这很厉害,非常会写。
蒋方舟:因为我从很小就开始写,我最早其实有一次经历近距离的观察死亡。
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下大雪,和爸妈出去公共的澡堂洗澡,在出门的时候看到对门门是敞开的,觉得很奇怪,但也不以为意,大概两个小时后回家,发现这个门还是敞开的,我妈就说你去看看,看看对门出了什么事。
然后我就进去看,发现对门的人头被砍掉,但是还有一点脖子连着,但是人是这样的,手在他的旁边。
陈丹青:你写了没有?
蒋方舟:我就写了。后来回看这篇日记,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手也被砍掉了。
陈丹青:你还在那儿看,没吓出尿来?
蒋方舟:没有,我在想他手为什么掉了,可能是因为他挡刀手掉了。
陈丹青:当时就会分析。
蒋方舟:名侦探柯南,包括血的形状在沙发上流的。
陈丹青:你一直站那儿看,根本没有掉头走?
蒋方舟:没有,因为当时每天都需要写东西,这个就当做今天有意义的一件事吧。
我就很认真地去观察死亡的样貌,而且具体的样貌到底是什么样的,包括沙发印花的纹路和血对它颜色的改变,我很认真地看了一会回去跟他们说,说那叔叔死掉了,你们报警吧,然后自己写了一篇日记去讲这件事,今天真是有意义的一天。
陈丹青:还在吗?
蒋方舟:应该还在,手写的,没有发表过。小时候觉得这种事没有意义,但是现在看好像有意义。
陈丹青:这是你第一次说出来吗?
蒋方舟:之前跟朋友讲过这件事为我是后来又看到这篇日记,当时的每个感触和细节,现在都能够通过我的部分回忆出来,我就是回忆当时这样的文本。
那时候开始可能对于我的经历和写作之间的联系,有一种很强的意识。我要怎么利用这个经历,像您说的我也觉得一个经历它没有被写出来,就像一个森林没有被看到或者一片海没有被看到,它似乎没有那么的有价值。
所以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我一定要把它写出来。

陈丹青:你保持说,我得消化消化,这比你写得那个还要可怕。
我们转话题,因为你还写到一个,我印象也很深,你去看文学家照片,对那些有名的倒不太介意,你讲了两个女作家。其中有一个叫做向田邦子,那篇写的非常好,但是我说不出来为什么写得非常好。
蒋方舟:就是写得好(笑)。
陈丹青:对,在看的时候在想你这样的看,看完了之后这样的想,大家都会做这件事情,我想在座所有人看人看事都会有感想,到书店都是聪明的。
但轮到写就完全两回事情了,最难受的是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材料被人写坏掉了,太多这样的例子了。
蒋方舟:尤其特别好的经历被他写坏了。
陈丹青:其实不重要,你们真的不要看重经历,因为我们太提倡一个"所谓生活",体验生活,这是神话。重要的是你说出来没有?第二你说得怎样?
我最在乎你说得怎样,你也很会说,最要紧的是还会变成写作。
其实你蛮克制的,我现在知道你其实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
没心没肺有一个好处,不会夸张,同时也会简练。有了这两个事情出来,事情的强度和重量就出来了,这是我看你的。因为我在检讨我自己的写作。
蒋方舟:因为您当时也发短信问我说,我是不是每篇改,反复地改,改到一个节制的程度,感觉非常有分寸感的写作。

我说其实每一篇都没有太改过,可能只是改过一遍而已,我后来想为什么?可能是我有长期写日记的习惯,记录自己每一次情感上的经历,巨大的事件,都被我当一个小学生当做今天是有意义的一天写下来的。
陈丹青:这不是理由,写日记的人有的是。
蒋方舟:但我写的时候,如果自己有太丰沛的感情或者太自我中心,我自己就会非常不舒服。
我其实还会回去改过去的日记,这一点做得不太诚恳,把日记当中写得太肉麻的,所有关于少女恋爱的部分全部抽干掉,只留下人物、地点、事件,留下我们说得话。
所以回看过程变成非常荒诞和冷静的文本,所以会回去篡改日记的手法,会把里边所有多余的感情去掉。
陈丹青:多大年龄?
蒋方舟:二十二三岁的时候。
陈丹青:那会你已经知道要改?
蒋方舟:那时候有意识地看过去的日记,比如那些太丰沛和太夸张的情感,我觉得太可笑了,所以我有意识的改自己的日记。
陈丹青:大学里正是在写这样日记的时候,你成熟得太早了点。
蒋方舟:有这样的意识吧。
陈丹青:我在想一个问题,因为我会想到张爱玲,我在想张爱玲如果要面对你今天遇到的事情,包括你前一本书,第一她会怎么写?
第二她属于三四十年代的人,足够处理她那时候的经验,但是一直不满足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其实很难处理,用文学和散文,虚构好、记实也好其实很难处理,这是讲不完的话题。
同时我也在想,在把你的东西跟她的比较,我会对你有个问题,你写作有多大野心?
蒋方舟:野心还挺大的。谦虚一点地说——其实也挺不谦虚的了,还是能写出能够把握时代精神的作品。
这是什么意思?并不是说写出一个卖得很好的作品,因为我觉得时代过去只有一两本书留下来。
陈丹青:你是说有一两本是你写的?
蒋方舟:至少有一两本是我写的,这是我写作的野心。
陈丹青:第二,你觉得怎么写才能有一两本留下来的书?
蒋方舟:首先需要对于当今社会的分辨和思辨能力,能够从复杂的五光十色每天都看似荒诞的东西当中,找到核心的东西,找到精神异化的源头,找到焦虑的源头,找到痛苦的源头。
另外我觉得还是不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隐藏起来,然后自己成为作品当中上帝。

陈丹青:艺术家。
蒋方舟:还有什么?
陈丹青:我不知道,当一个作家评论你的绘画也好、作品也好,他说你是有野心的,这是一句夸你的话,也是一句问你的话。
有时候在你的作品里边立刻看到你的野心,有些不是一下能看出来的。
蒋方舟:从文本里你有看到我的野心吗?
陈丹青:在我的同代人身上都看到,但是我读不完我同代人的书,除了阿城,蛮少读完任何一个50后的小说。所以你应该很明白我的意思,我很在乎怎么写。
我在你的书里还是看到一个对我来说很矛盾的经验,一方面你刚才已经说了,了解这个时代、分辨种种差异,包括是非、包括荒谬种种,我现在都没做到,你已经做到了。
第二我又要归结到最最具体的东西,就是画画,跟画画道理是一样的。我看一个人的画,根本不看他画什么,我先看他笔头老不老,我看文字也是这样。
我现在看你的东西和包括看70后,50后也一样,不太容易看到笔头老的东西,像张爱玲十几岁笔头就很老,我很惊讶。
我也很欣赏阿城,他写威尼斯日记的时候是40岁左右,笔头就很老。
但是我知道是一种偏见,比方说我喜欢读鲁迅,我喜欢他有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就是笔头老,像南货店一样,江南人的说法,有时间、亘古的,上海话叫有嚼头。
我在想,我该不该要求你的笔头老,可能把它错当成一种写作的野心或者把它跟前一代作家去比。
蒋方舟:笔头老反面的表现是什么?就是说会觉得浅?
陈丹青:就是笔头嫩。王安忆做过一个比喻,他说我们这代人还是草鸡,70后鸡叫什么?叫鸡栏里养大的,饲料里养大的,这既没有贬义也没有褒义,你们的成长经验,你们所有体验的鸡地真的是体验的鸡地,就是草鸡和草头。
蒋方舟:我理解您说的,也然后想到说张爱玲写香港打完仗之后,大家都喜欢结婚和吃东西,那篇文章特别喜欢,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拿出来读。

陈丹青:问题是张爱玲在她的年代十几岁拿出笔头老不是太稀罕的事情,你要知道我母亲是那一代人,我现在回想,我的浙江亲戚,我所知道的大人,看他们的信,笔头老是一个常态,因为他们的语言都很老,现在这种语言没有了。
为什么母亲死了我很难过?用那样的语言跟我讲话的人没有了,我的同辈已经不能用这种语言跟我讲话,晚辈更不可能,这是一种享受,再也没有了。
我相信欧洲和美国也是这样的,日本也是这样的,但是我看欧洲的写作托尼·朱特,我相信翻译都能感觉笔头老。
蒋方舟:《思虑20世纪》。
陈丹青:所以每一本我都要看,这是我不读小说的原因,绝大部分小说都不读,故事延续的非常好,但我要的是一入口的滋味。
蒋方舟:大概有过类似的体验,我觉得像中国的作家,当然他们用的词是捕捉时代,但我觉得看到的其实是一种应对,其实是一种更为被动的应对,在面对试图去书写的时候,好听一点说看到了野心,但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应付不来的或者是对于时代的追赶吧。
我脑海当中有一个更感性的感觉,但我把它表达不出来,我觉得这种笔头老的文字可能以后也很难的。
陈丹青:我想说,你这不是笔头老的写作,也绝不是你的问题,整代人都不是那么写的,我不该说你们不能写,而是你们不再这样写了,这可能是件好事。
对于一个新的语言、新的文风,集体的一种文风会出现,其中会出现一些天才,一些出类拔萃的人。我为什么能够全部读完你的书?我拼命在改变我自己,对我自己来说这是一种偏执。
你的东西很软,所有人的东西都很软,现在80后的讲话非常软,没有辣椒的,全都是淡淡的,甜甜的。
但你这种笔风和语言风格里边,时不时的会让我吃一惊,事情的意思、味道全被你说出来了,但用的是我没有习惯的文风。
所以当我问你有没有野心的,其实有点错位,我还是拿我对上一代的阅读记忆来想往这上头找,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蒋方舟:太让人挫败了。
陈丹青:你也这样,我可能选了一个不对的点就是笔头。你为什么找我呢?你应该找一个比方说至少70后或者80后,甚至你有点吃醋或者在吃你的醋,但是你们俩又其实很钦佩的人玩一把。
蒋方舟:因为我觉得70后、80后太容易找到共性了,包括独自在异国的孤独或者是为什么写作,太容易找到情感上的共性和可以沟通的地方,但我希望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年代、一个陌生的目光来谈论。
这样能够让我变得比较不狭隘,所以我刻意找一些,比如说也参加项目,有声有色地去日本。
陈丹青:我很佩服你怎么写得很简单,但是份量一点不轻,我很生气。我写到自以为重要的经历太用力了,太当回事了,但是你也没有不当回事,你其实够了,不要让读者读那么多东西。
蒋方舟:自己其实也是有意这样,如果感觉到情感的份量是10分,比如说从别人的死亡当中,特别是自己崇拜的死亡当中,自己感受到的情感是10分,但觉得读者接受到其中的一两分,对我来说其实就足够了,不想10分的传递给他们。
因为我觉得当他低估情感分量的时候,我会很难受。所以我觉得宁愿传达出来只有其中的1/10、2/10,在处理里边所有对我来说重要的事情,我都刻意地把它情感的份量削减一些。
【相关图书】
《我承认我不曾经历沧桑》

蒋方舟二十岁后,首度杂文结集。
反思成长道路上的得与失,描画身旁被绑架的一代群像,重寻写作的意义。
《东京一年》

这是蒋方舟东京生活一年的四十六则日历,收录了她最新的短篇小说、演讲和时评,驳杂不失纯粹。
从社会、艺术到当今中日两国世间百态,都有其独特又不失严肃的描摹与思考。
转载::后台回复“转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