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自话题:蒋方舟日本


蒋方舟说,只有看书的时候,生命的体验才会变得逐渐丰盈。
“知识分子或艺术家,终其一生所做的就是输入和输出,读书对于我是输入,写作对于我是输出,就是这么简单。”
文/苏马
在《新周刊》广州总部工作时,蒋方舟的爱好之一是看路边民工。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学校外面的黑车司机也是她的观察对象,她特别喜欢听这些人聊天,看他们的日常。
这种重复的呆滞与出神也出现在张爱玲的经历里,蒋方舟在一些作家的描写中读到,张爱玲常杵在路边看工人修高处的电线杆,一看就是半个多小时,“我也有点这样,不过不是看电线杆”。
蒋方舟7岁开始读张爱玲,现在还在读,“过段时间就会看看,她的每一个字句、每一个比喻都已经烂熟于心”。7岁写作、9岁出书,从小被打上“神童”“天才少年”等标签,她时常觉得自己像个马戏团表演者般被围观,是一个站在低处的被参观者。
她对张爱玲作品或经历中的“冷淡”与“拒绝”很有共鸣。“读到她的一些行为,我会觉得,噢,原来她也这样,然后觉得我干一些事情也是合理的,不会责备自己。”

蒋方舟的高中岁月,是在江城武汉度过。
二十年后的现在,蒋方舟感叹,潜移默化之中,早年读过的只言片语塑造着她理解世界的方式。“确实,并不是能被大众接受的才是好东西,很多非常珍贵的情感只有少部分人能体会。”她越来越认同尼采的那句话。
大学期间,蒋方舟有过一段轻度抑郁的时光。“整天待在宿舍,怕和人交谈,厌世畏人,不敢去食堂,凌晨才去自动贩卖机买油炸花生吃。觉得自己胖、丑,觉得他人都在笑我太‘卢瑟儿’,觉得生无可恋。后来强迫自己每天出门,写东西也要去咖啡厅,每天听点人声,人笑时我也模仿着笑,慢慢地好转了。”好几年前,她在微博上自揭伤疤。
自救的重要方法是阅读,她说只有看书的时候,生命体验才变得逐渐丰盈起来。从小暴露在公众视野,她并不是一个外向的人,她害怕冷场,害怕失望,参加聚会或公开活动,如果在场的其他人不说话,她会通过“呕吐式自曝情史”等方式来填充沉默。

蒋方舟在清华大学的毕业照。
她曾在电视访谈里笑着自嘲为谄媚型人格,一边这么说,一边内心感到无限的消耗与孤独。她认为,真正外向的人与话多话少无关,一个外向的人可以很沉默或者面无表情,却发自内心享受与人相处交谈的过程,而她完全相反,即使别人觉得她笑得很开心。
所以,她信赖阅读。在她看来,读书与看电影、电视不同,看影视剧时是一种被动的接受,不管视觉技术多么好,人们会很清楚地知道眼前的一切是假的,知道几个小时后故事就结束;而阅读是很私人的体验,阅读者通常会随着文字沉浸到情节中。
“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的时候,写到结尾突然放声大哭,朋友问他为什么如此伤心,他说包法利夫人死了,朋友觉得奇怪,既然不愿意女主角死去那就把她写活过来呗,福楼拜无可奈何,说没有办法,他没想把她写死,但写到结尾,生活的逻辑让她非死不可。”蒋方舟说,这种体验对于作家都是未知的,何况读者。
“你也不知道你笔下的人会把你带到哪里去。”在她眼中,阅读以及写作都是一个人的冒险,冒险过程中会发现许多自己内心不曾被发现的隐秘部分。
读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时,蒋方舟感受到一种不可逆转的时间流逝,仿佛这一生所有的悲伤、失落、无助、惶恐都凝聚在阅读的短短时间里,“你的感情在小说里面投射,随之波动”。
蒋方舟观察到,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一直做着自己并不太认可的工作,他们顺从并追赶着所谓时代的价值标准,相信只要每天往前走一步,就是在进步。可能人到中年得到了世俗上的成功,但突然有一种无以名状的悲伤,再然后只能通过马拉松、登山、摄影或者搞外遇来消解这种中年悲伤。

蒋方舟的书房。
在书里获得某种情感体验与自我审视之后,对人性的理解会变强,对他人的苦难有更强的共情能力。
蒋方舟出生于1989年下半年,按照现代社会的划分标准,中年离她还很远,但读到小说里的伊万,她提前感受到中年式恐惧与自省。她不停地思考,自己所在的火车到底是不是在往前开,是不是在盲目地跟着时代洪流往前走?
一改最初以自我观察发表公共意见的杂文风格,蒋方舟这几年在尝试小说创作,2014年,她出版小说集《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书中收录了9个互有关联的故事,涵盖中年人、死人、灵魂等视角,不乏褒贬。她自己也有遗憾,说当时出版周期太赶了,如果再改个半年,最终出来的作品可能会更成熟。
当时小说出来后,有人质疑天才少女不过如此,朋友笑她“自己挖的坑得自己跳出来”,她回答:“确实如此,而且不可否认,我在这个少年成名的坑里吃了不少观音土,是这个坑的受益者,获得了比别人更多的关注和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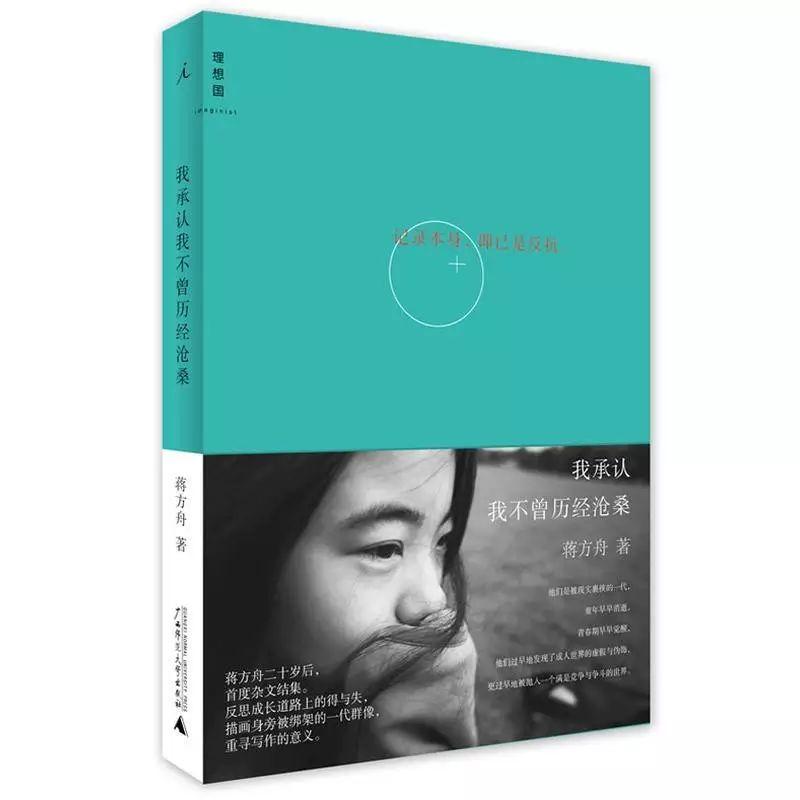
蒋方舟出过本书,叫作《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这个标题也像是对自己的注脚。
蒋方舟把跳坑的过程比作游泳场地的变化。她说像过去那样写杂文是在游泳池里游泳,那里熟悉、舒服、安全;创作小说作品则是游向未知的大海,那里不再安全、确定,但那些不确定中或许有解决焦虑的可能。
当“以前年轻时”“现在年纪大了”等句子频繁出现在她嘴边时,你明显感受到一个青年作家的时间焦虑。“你看看歌德28岁写了什么?当然这样说有点不要脸。近一点,可以看余华、苏童28岁时写了什么,这种东西会让我真的觉得焦虑。”她说,尽管自认在每个阶段都尽可能地使出全力投入创作,却未达到自己理想的标准。
小说的世界感性而丰富,在书里获得某种情感体验与自我审视之后,对人性的理解会变强,对他人的苦难有更强的共情能力。“那之后,你可以有一个自由去选择要走什么路,要成为什么人。”蒋方舟说,很多人对于外部世界没有那么好奇,每天纠结在一些琐碎的痛苦之上,就是因为缺少这种过程,逐渐丧失了对于他人苦难的理解能力。

少年成名的八零后作家群,现在纷纷迈过或者将要迈过而立之年。
看书摘录是她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入口,也是表达的切口。
阅读是蒋方舟对抗焦虑的方法之一。读者会发现蒋方舟常常分享类似的阅读体验,并且喜欢引用他人的原文。当她在杂文集《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中描述中产阶级的孩子时,引用的是小说《红字》里的话:“倘若世世代代都在同一处不再肥沃的土地上反复扎根,人性就会像马铃薯种在这片土地般无法繁茂茁壮。”
在谈话节目《圆桌派》中因婚恋观被误解后,她引用清华学姐刘天昭的话:“不要和愚蠢的人自嘲,他们会当真的,然后在你面前傲慢起来。”
为了记住读过的好句子,她从大学起不断摘录。平时读到有意思的内容,蒋方舟会先用手机拍下来,等到晚上回家再打开电脑誊抄整理。她习惯在摘录里记上原句和阅读感受、联想等,每天如此。

蒋方舟作为嘉宾参加《圆桌派》。
“你看了书,它会对你产生影响,你偶然想起一个句子或一个点子其实并不是你的。正常的话,摘抄下来后,你会清楚地知道那句话是谁说的,而不会误以为是自己的就把它想当然地写上去。”蒋方舟说,宁愿全部原文引用,也不愿意在明明知情的状态下,化用别人的智慧来假装自己的想法,除非自己有把握比原文说得更好,否则那是一种不道德的“偷”。
在搜索引擎与电子信息触手可及的年代,一般人可能会认为重复摘录的过程如同苦行僧修行,蒋方舟自己于此却无特殊感受,她说阅读跟吃饭一样普通,没有必要刻意用它陶冶情操或平复心情。
“有时候写到下午两三点,有点累了,可能就看一个小时小说,再继续写。” 她自述过着极为规律的生活,上午九点多十点起床,在家吃个饭,然后出门到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坐下,打开电脑写东西,写到傍晚回家吃饭,跳跳操,跟妈妈聊会儿天,再看看书或者漫画,然后12点睡觉。

蒋方舟与母亲尚爱兰。
她喜欢在写作间隙翻阅的小说是威廉·福克纳的《熊》。“猎人们还讲关于人的事,不是白人、黑人或红种人,而是关于人,猎人,他们有毅力,不怕吃苦,因而能够忍耐,他们能屈能伸,掌握诀窍,因而能够生存……按照古老的毫不通融的规则,进行着一场古老的永不止息的竞争。”为了一个阅读活动,她在常去的咖啡馆对着录音笔读起喜欢的段落。
念完,她解释,这个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但描写得特别生理,读起来“嘴里因为紧张,而有了金属的味道”。
蒋方舟现在27岁,去年重返校园读写作方面的研究生课程,穿着打扮散发着学生气质。如果坐在她不到一米的距离面对面观看,会清楚地知道她几乎没化妆,脸上除了粉橘色口红基本素颜,一头过肩中长发自然披散,没有刻意整理过的痕迹,尽管她早被告知采访结束后需要拍照。某种程度,这和妆容素净但喜欢娇艳口红的张爱玲很像。
蒋方舟的推荐书单
1《恶棍来访》(珍妮弗·伊根)
2《自由》《纠正》(乔纳森·弗兰岑)
3《刀背藏身》(徐皓峰)
4《炸裂志》(阎连科)
5《微不足道的生活》(伊丽莎白·斯特劳特)
6《亲爱的生活》(艾丽丝·门罗)
7《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村上春树)
8《枯枝败叶》(加西亚·马尔克斯)
9《纠结的感觉》(朱利安·巴恩斯)
10《父亲的眼泪》(约翰·厄普代克)
说到读书,听听白百何怎么说?
点击图片打开


标签组:[蒋方舟] [读书] [文学] [小说] [张爱玲]
上一篇:蒋方舟:我是这样考上清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