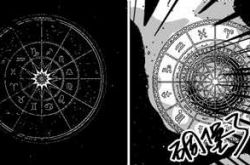发表自话题:富春山居图
关于完整的富春山居图的解读
【前言】
1、缘起 2010年,庚寅年。在“凤凰卫视”上看到台湾学者蒋勋先生解读《富春山居图》,受到启发。除较详细地阅读蒋先生的书稿之外,又收集并阅读了一些相关的文献。还写了相应的“学习报告”一类的小文,送给朋友交流。但是,自那以后,头脑中就渐渐产生了一些“?”。几年来,常常会想起这些“?”,但并没有引起“兴趣”来。近日,不知哪儿来的“一阵风”,吹皱头脑中的“一池清水”,使我拿起这些“?”,企图搞搞清楚一点。以此与朋友们交流。
2、《富春山居图》是元朝画家黄公望
为郑樗(无用师)所绘,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一幅山水长卷,乃黄公望的代表作,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明朝末年传到收藏家吴洪裕手中,吴洪裕极为喜爱此画,甚至在清顺治七年(1650)临死前将此画焚烧殉葬,被吴洪裕的侄子从火中抢救出,但此时画已被烧成一大一小两段。较长的后段称《
无用师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前段称《剩山图》,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富春山居图》2011年
6月在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用技术手段将《剩山图》与《无用师卷》“无缝”连接后称为“合璧图”。
3、《富春山居图》作者:黄公望
元代画家黄公望
(1269--1354),字子久,号一峰,大痴道人,常熟(今属江苏)人。擅长画山水,多描写江南自然景物,以水墨,浅绛风格为主,与吴镇,王蒙,倪瓒并称元四家。原系浙西廉访司一名书吏,因上司贪污案受牵连,被诬入狱。出狱后改号“大痴
”,从此信奉道教,云游四方,以诗画自娱,并曾卖卜为生。他学画生涯起步较晚。然由于生活坎坷,寒暖自知,所绘山水,必亲临体察,画上千丘万壑,奇谲深妙。其笔法初学五代宋初董源、巨然一派,后受赵孟頫熏陶,善用湿笔披麻皴,为明清画人大力推崇,成为“元四家
”(王蒙、倪瓒、吴镇)中最负众望的大画家。此外,画作之余,留有著述,如《写山水诀》、《论画山水》等。
 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起始部)
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起始部)
 剩山图
剩山图
一、《剩山图》是《富春山居图》的卷首吗?
1、蒋勋先生的“解读”
正当《剩山图》将要赴台湾与《无用师卷》联展时,台湾著名学者蒋勋先生这样解读:
“五十一点四公分,它是贝多芬交响曲里的“当当当当——”,他一定要有一个起句,没有这个起句后面没有办法开始;它也是李白写《蜀道难》,“噫吁唏危乎高哉”五个短音节,重音,有重音才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样的后面一个长诗出现。所以这是一个结构上的问题,使得我们对于2011 年6月这样的一个合璧有非常大的期待,有非常非常大的重视,因为它等于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画作,重新可以放在一起,我觉得黄公望地下有知,大概会非常开心这件事情,因为它的结构可以重新被理解。”
“。。。。如果我们刚刚了解了贝多芬的当当当当的重要性,它一定要有一个重音,敲门的重音,所以从这里开始绝对是有问题的,从结构上,因为这么长的长卷,等于是一个大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一开始一定要讲一个大的神话,女娲补天,然后才开始这个小说,所以这个我们叫做起句,在结构上的这个重要性。所以我们还是再把它接一次,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这一次接在一起以后,它对我们整个了解绘画的这个重要。” 无疑,蒋先生认为《剩山图》就是《富春山居图》画面的卷首(即全图的起始处)。
2、《剩山图》并不是《富春山居图》的卷首—— 富春山居图的被烧毁的五尺
据记载:吴洪裕(问卿)“火殉”一事,使他成为《富春山居图》卷乃至中国美术史上的罪人。“其从子吴静庵疾趋焚所,起红炉而出之… …”,然而由于火势太猛,经吴静庵抢救出来的画卷,已断裂去前面五尺许。中间烧出数个连珠洞,并断成一大一小两段。被烧毁的五尺,画的是城楼隐约,平沙无垠,为富春江口出钱塘的景色;五尺之后,才是峰峦云树,坡石起伏。吴静庵救出此卷后不久,经由当时极富修复能力的古董商人吴其贞之手,将烧焦的部分细心揭下,发现还有尺许画卷完好,重新接拼后,居然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几乎看不出是经剪裁后拼接而成的。这尺许完好画卷,为吴其贞所得,就是《剩山图》。
由此可见《剩山图》不是《富春山居图》画面的卷首(起始的画面)。
3、被烧毁的部分画面是什么样的?
3-1邹之麟 仿《富春山居图》
那段画面已经“灰飞烟灭”,无法复原。明清之間,沈周、王時敏、張宏、周世臣、沈顥、鄒之麟、唐宇昭、程正揆、王翚皆有臨本,因各具風神,故亦為世人所重。其中鄒之麟一卷,因作者曾多次在宜興吳家處見過原作而臨倣的“火前”副本,故當時已備受重視,此卷之鱗自識臨于辛卯冬日,徐邦達先生考為黃公望原作被焚後一年。
由於黃公望《富春山居》原卷已殘,後人一直企圖從明清諸家的摹本中窺其全貌,但據饒宗頤先生考證,目前能見到的各種摹本,皆缺去起首平沙五尺余一段,“此本(鄒之麟臨本)平沙五尺余宛然在目,故知惟有此鄒氏臨本方是完本。”清初惲南田也這樣說,“鄒衣白先生有拓本……庶幾不失丘壑位置。”這種“不失丘壑位置”的“完本”,使鄒氏臨本成為歷來研究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必不可少的重要資料。
邹之麟不但多次在吴问卿家欣赏过《富春山居图》,而且在留有题跋,写道:“余生平喜画师子久,每对知者论,子久画书中之右军也,圣矣!至若富春山图笔端变化鼓舞,又右军之兰亭也!圣而神也。海内赏鉴家愿望一见不可得。余辱问卿知,凡在三见,窃幸之矣!……。”。可见,邹之麟不止一次欣赏过《富春山居图》。也正是他提出《富春山居图》是画中的《兰亭序》。这一说法,曾被乾隆借用,使得后人误以为是乾隆的一大“发明”。
 邹之麟 仿《富春山居图》
邹之麟 仿《富春山居图》
3-2 沈周仿富春山居图
画卷在数百年流传中饱经沧桑。至明成化年间,由沈周收藏。沈周自从得到这件宝贝,就爱不释手,把它挂在墙上,反复欣赏、临摹。看出画上没有名人题跋,沈周便请朋友题跋。一朋友儿子见画画得这么好,就产生歹念把画偷偷卖掉,还愣说画是被人偷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沈周在画摊上见到了《富春山居图》,兴奋异常,连忙跑回家筹钱买画。当他筹集到钱,返回画摊时,画已经被人买走了。沈周捶胸顿足,放声大哭,可是后悔已经晚矣。千辛万苦弄到手的《富春山居图》,如今只剩下留在头脑中的记忆了。沈周愣是凭借着记忆,背摹了一幅《富春山居图》一卷以慰情思。
下图是这幅画的卷首部。
 图2 沈周
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 纸本设色
36.8×855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2 沈周
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 纸本设色
36.8×855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3-3张宏仿《富春山居图》
明代画家张宏在临仿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时,该图还是完整的画作,尚未被焚,所以后世将张宏这幅《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看作是研究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重要版本。
 张宏临仿《富春山居图》
张宏临仿《富春山居图》
二《富春山居图》中有几个人物?
1、《富春山居图》中有“八个人物”:1、桥上的“走向未来”;2、山林中的“樵夫”;3、渔夫;4、草亭中的“读书人”;5、又一渔夫;6-7、两只小船上的人;8、桥上往回走的人。理解“渔樵传统”,“云、水、路”以及“周而复始”的时间观念等等。细品才能领悟画之“意”。
2、蒋勋先生说:有七个人
蒋勋先生的解读如下:
“……这张画一共有七个人,过去我常常给我的学生期中考就说到,黄公望富春山居前面去找找看,找到七个人就一百分,那现在还没有人找到过。你大概看到这个人很容易,第二、第三、四个人很容易,有三个人是在山里面,你看不到的,等一下我们也会把他们放大,也许大家可以在现场里面去找一下这几个人物。
渔夫在江上钓鱼,茅亭里有一个读书人,他们两个在对望,中间有一群鸭子。我把下面这一段放大,鸭子、渔夫,渔夫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从这个地方到了这个地方。……
。。。。我们这里又看到一个人,这是我跟大家提到大概最容易找到的三个人物,可是这个人姿态动作形象都跟刚才那个非常相像,所以是刚才那个人到这里来了吗?如果是刚才那个人到了这里,那意思说他不是两个人,他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间你会在不同的位置。这样可以了解,因为它是长卷,长卷不是摄影,长卷是电影,它里面用了很多蒙太奇的方法去剪接了。(【注】:黑体字是本文作者“加黑的”)时间里面不断的连续,有时候可能是倒叙,有时候可能是对未来的幻想,所以这些东西在交错。所以1895年有了电影之后,其实用它来理解东方的长卷是更好的方法,因为西方的画画,一定站在那边,闭起一个眼睛这样比来比去,因为他在找焦点。你从来没有看到张大千需要这样画画,因为他就是坐在船上,玩了一玩以后,回来靠记忆画画,他不是在找焦点。如果焦点,那个叫焦点透视,没有办法真正扩远。黄公望一直讲扩远,是要宽阔出去的远,那个要散点透视,他必须放大出去,所以他只有电影能够解释,这样的一种空间形态。
原来,蒋先生知道图中画了有八个人物,不过他认为其中第五个人物和第三个人物是同一个人,因此,他就说《富春山居图》中“一共有七个人”。
三、刍议
1、残卷不能代表完整的《富春山居图》
解读《富春山居图》,应当是解读完整的《富春山居图》。现存的《剩山图》与《无用师卷》连接在一起的《合璧图》,依然是“残卷”,不是完整的《富春山居图》。《剩山图》更不是《富春山居图》起始处。
《剩山图》前面是什么?已被火焚,灰飞烟灭。但是,从一些文献记载以及对火焚前的《富春山居图》的临仿本可以判断:被火焚的那一段应当是“平沙无垠,富春江口出钱塘的景色”。
既然《剩山图》不是长卷的起始,那么就不会有“它是贝多芬交响曲里的‘当当当当——’,他一定要有一个起句,没有这个起句后面没有办法开始;它也是李白写《蜀道难》,“噫吁唏危乎高哉”五个短音节,重音,有重音才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样的后面一个长诗出现。”
也正是这样,我们这些后人们也不可以这样解读黄公望创作《富春山居图》时的心境和创作思路。更何况,黄公望信奉道教,一位“出世者”,怎么会有贝多芬、乃至李白那样的叙事“风格” 呢?
把《剩山图》当作《富春山居图》的起始来解读,颇有“断章取义”之感觉。
2、“写意”与“写实”
《富春山居图》是一件以富春江为背景的传统山水画,虽然描绘的是富春江的景色,但他是“写意”,不是“写实”的,即在“似与不似之间”。更重要的是,作者借景抒情,用绘画表达“心境”。此乃和西方“写实”的“风景画”的根本不同。
黄公望在《富春山居图》中表达的是他的什么“心境”?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只有他自己清楚。而对于《富春山居图》的观者而言,可以说“一千个人有一千个解读”,“解读”就是在观者头脑中的“反应”,因人而异。有“靠谱”的,也有“不靠谱”的,难免也会有“忽悠”的,这都没有什么。如果把这种“解读”放在公众面前,有不同的评论也是自然的、正常的。不过,过度的“解读”,其结果是“过犹不及”。
3、透视—焦点透视—散点透视—电影?《富春山居图》中有几个人?
近代,“西学东渐”,不乏有用西方的“科学理论”解释中国传统艺术的,其中:“中国画是‘散点透视’”就是一例。
据说,德国人,Otto Fischer 在著作《中国风景画(Chinesische Landschaftsmalerei)》中首次提出“散点透视法”这个说法。将此说法引入到国内的可能是学者宗白华。之后被逐渐使用开来。
文人墨客们好像觉得:这样一来,中国传统画就有了“理论根基”而“科学化”,进而“现代化”了。
其实,“散点透视”是未经过科学验证,只是一个猜想和假设。中国传统画中没有“透视”这样的概念,在古代《画论》里更找不到“散点透视”,虽然对于“近大远小”的认识很早就有,比如——
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指出:竖画三寸, 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远。
王维在《山水论》中,有:“丈山尺树,寸马分人,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石,隐隐如眉(黛色),远水无波,高与云齐。”
到了宋代,郭熙提出“三远”,即“高远、平远、深远”,之后韩拙又提出“阔远、迷远、幽远”。
这些“画论”,与来自西方的“透视原理”无关。
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传统的中国画不讲究“写实”,而是“写意”。所谓“似与不似之间”。
从透视学的发展史上看,透视就是一门科学与实践的学科,它是西方绘画术语,是根据物理学、光学、数学原理,特别是投影几何的原理运用到绘画中来的专业技法理论。它和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意象”搭不上界。
有人戏谑说,所谓“散点透视”,就是“自编”。不错,中国传统山水画是作者把自己头脑中的“山川精华”浓缩后,一个一个拼接起来,以表现山川的景象。
尽管,现在有些山水画教学中,特别是画中有“亭台楼阁”之类的建筑物时,也引进了“透视”的技法,例如,画面上的建筑物的透视“消失点”要在同一视平线上。这仅仅是一个很有限的改进而已。
我们不必自卑,不必将传统艺术披上“科学化”的西装。
后来,在解读传统画“长卷”时,又出现了“长卷”与“电影”的联姻。似乎在中国,“电影”的技巧老早、老早就有了,比西方要早得多得多。
其实,动态的“电影”与静态的平面上的画面二者之间,无法相提并论。
电影是运动,是动态的表现形式,怎么会有静态的构图?如果我们把绘画撇开,单独来研究电影的视觉问题,我们就会发现,电影所表现的是一个运动的空间。电影最重要的就是运动: MOTION 。电影的学名应叫 MOTION ICTURE ,活动映画,或 CINEMA 。这些概念强调的都是运动。
在电影中观众视觉中反映的是运动幻觉和立体幻觉。
银幕上并不存在真正的运动,因为每格画面都是静态的。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了运动。
然而,影视是迄今为止最真实的艺术,她不仅能逼真地再现生活中静态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而且还能真实地纪录运动中的飞禽走兽。然而这种“逼真性”和“运动性”的特征都是建立在幻觉的基础上的。
写实的、运动的,给人以幻觉的,这就是“电影”。它和传统山水画长卷如何“联姻”?
中国艺术中的时空不是物理的,是意象的、心理的。可是电影恰恰是摹拟物理的时空,所以中国人从艺术的角度来理解电影的物理时空有一定的困难。很容易就“文不对题”。
由此也就产生了《富春山居图》中“有几个人?”的问题。
由于现今能看到的是“残卷”,火焚的那一段中,有没有人物?无从谈起。但是存下来的画面上的,的的确确有八个人物,而不是七个人物。
为什么蒋勋先生认为是只有七个人物呢?他认为《富春山居图》就像“电影”,画面中第五个人物和第三个人物“很像”,因此是同一个人,只是移动了位置。这一说法有点令人惊诧。《富春山居图》虽然长达数米,尽管有丰富的内容(山水、人物),但它依然是一幅画面,怎么是用摄像机记录下来的“电影”呢?传统山水画的所谓“散点透视”与近现代的“电影”能挂上“钩”吗?用西方的、乃至近现代的“帽子”往往黄公望头上戴,似乎几百年前的黄公望已经运用了“电影技法,乃至蒙太奇”,这未免太“奇”了点儿吧!?
《富春山居图》中的人物是用极简的笔法画出来的,无所谓“像”与“不像”,
因此不可以说第五个人物(小船上人)和第三个人物(小船上的人)就是一个人。如果由此推理,可以得出另外的解读,最极端的结论是:现在能看到的《富春山居图》上只有一个人物,而且可能就是作者本人,一位生活在富春江畔的“出世者”的生活写照,或者说是他的“理想境界”:打柴、养鸭、读书绘画、捕鱼、与友人一同游览江上风光。能不能这样推论吗?也未尝不可。
解读,毕竟是解读。现在留存下来的《富春山居图》画面上有“八个”人物,而不是“七个”。
个人之见,难免有误。虽学绘画,半瓶子醋。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如得指点,幸甚!
2016年6月24日星期五 于树锦行空居
2016年7月2日星期六 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