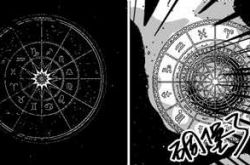发表自话题:闲淡抄人
原标题:郑利华 | 苏轼诗文与晚明士人的精神归向及文学旨趣
在晚明文坛,苏轼俨然成了一位颇受关注的人物,更多进入士人的视界,文士圈中阅读、评述、刊行其诗文者层出。后七子领袖人物王世贞曾于万历年间编辑《苏长公外纪》,他在该书序文中表示,“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独苏公之作最为便爽,而其所撰论策之类,于时为最近,故操觚之士鲜不习苏公文者”[①]。此番褒扬苏轼文章之言,不啻为编者本人推尚苏氏的表白,如其自言“意似好其人与其事,聊为纂集”[②],且也道出了当时文人学士嗜好苏氏之作以至“鲜不习苏公文者”的情状。焦竑在《刻苏长公外集序》中则指述“顷学者崇尚苏学,梓行寖多”,并且因为时人热衷于编刊苏轼诗文,甚至“或乱以他人之作”,由是不免“纪次无论,真赝相杂”[③]。陈梦槐《东坡集选》卷首所录“集选长公文诸家姓氏”中,除王世贞之外,尚有李贽、钱士鳌、陶望龄、袁宏道、王纳谏等晚明之士;又据万历至崇祯年间所刊苏轼诗文诸选本,以及相关序跋文所载,他如当时的徐长孺、凌濛初、钟惺、谭元春、焦竑、崔邦亮、郑圭、凌启康、闵尔容、吴京、朱之蕃、陈仁锡、陈绍英等诸士,也曾参与苏氏诗或文的选辑[④],各类苏轼诗文选评本大量涌现[⑤]。这多少反映了苏轼诗文在晚明文坛的流行情势。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尤其在晚明文士圈中呈现的这一“崇尚苏学”的趋势,究竟是在何种文学境域下展开的,苏轼诗文和晚明士人的精神归向及文学旨趣之间,究竟构成怎样的一种关联,并藉此冀望对于深入认识晚明文坛的发展势态及精神内涵有所裨助。
一、“崇尚苏学”与宋代诗文的再审视
纵观有明一代不同时期诗文的宗尚统绪,特别是自弘治和嘉靖年间以来,随着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诗文复古流派的相继崛兴和扩张,诗主汉魏、盛唐,文主先秦、两汉的诗文基本宗尚系统得以确立。与之相对,尤其是基于反宋学的立场,宋代诗文则成为复古派成员及其追从者重点排击的目标,这已是明代文学史上众所周知的事实。时至晚明,伴随文学复古思潮的逐渐回落以及变革呼声的增强,由复古派及其追从者确立起来的诗文宗尚系统,乃更多受到质疑以至被突破,这其中,曾经为他们极力鄙薄的宋代诗文,则在此际相对开阔或多元的文学境域中得到重新审视。
应该说,晚明文士对于宋代诗文的认知,尽管从总体上来看超离了此前确立于文坛的较为单一和偏狭的宗尚界域,而多出自相对开放、活跃的知识接受及精神诉求,然鉴于各自不同的阅读经验和审美趣尚,这种认知在诸文士那里又并非完全表现为不二的共识,而事实上呈现不同程度的差异性。以公安派代表人物袁氏兄弟为例,如袁中道曾撰《宋元诗序》,述及作者关于宋诗乃至元诗的基本态度,提出:“文章关乎气运,如此等语,非谓才不如,学不如,直为气运所限,不能强同。故夫汉、魏之不《三百篇》也,唐之不汉、魏也,与宋、元之不唐也,岂人力也哉!然执此遂谓宋、元无诗焉,则过矣。”这无非是说,宋、元诗歌之所以不同于唐诗,主要受制于“气运”而非作者才学,故不可谓宋、元无诗。并且以为,宋、元诗歌“取裁肣臆,受法性灵,意动而鸣,意止而寂。即不得与唐争盛,而其精采不可磨灭之处,自当与唐并存于天地之间”[⑥]。凡此,又无疑在声张宋、元诗歌独特之风格,以及为其与唐诗相“并存”的合理性作辩护。在另一方面,袁中道并未因此忽略唐诗尤其是盛唐之作的典范意义,其《蔡不瑕诗序》指出:“诗以三唐为的,舍唐人而别学诗,皆外道也。”[⑦]在《寄曹大参尊生》书札中他又表示:“盖天下事,未有不贵蕴藉者,词意一时俱尽,虽工不贵也。近日始细读盛唐人诗,稍悟古人盐味胶青之妙。”[⑧]以故其教人习诗,曾主张“但愿熟看六朝、初盛中唐诗,要令云烟花鸟,灿烂牙颊,乃为妙耳”[⑨]。即使是那篇多为宋、元诗之价值地位进行申辩的《宋元诗序》,其文开端也提出,“诗莫盛于唐,一出唐人之手,则览之有色,扣之有声,而嗅之若有香。相去千馀年之久,常如发硎之刃,新披之萼”,相比之下,宋、元诗歌则“不能无让”[⑩]。总之,在认肯宋诗乃至元诗特点及其与唐诗比较的问题上,袁中道基本采取的是一种较为理性、平允的态度。
相较起来,袁宏道对于宋代诗文的评述,则明显表现出为矫革时俗而针锋相对的偏激之态,用他的话来说即所谓“多异时轨”[11]。如他万历二十六年(1598)在答陶望龄的书札中谈及自己“遍阅宋人诗文”的心得,以为“宋人诗,长于格而短于韵,而其为文,密于持论而疏于用裁。然其中实有超秦、汉而绝盛唐者”,“夫诗文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欧、苏矫之,不得不为巨涛大海。至其不为汉、唐人,盖有能之而不为者,未可以妾妇之恒态责丈夫也”[12]。在为江盈科《雪涛阁集》所作序文中,论及诗歌之法的变化问题,他又指出:“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见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这里,作者无论是申明宋代诗文乃有“超秦汉而绝盛唐者”,抑或强调宋诗“因唐而有法”,其基本立场,还在于反逆倡为“复古之说”的“近代文人”[13],刻意颠覆其说的意图显而易见,犹如袁宏道在致张献翼的一书札中所云:“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14]然如此眷顾宋代诗文,并不意味袁宏道已专注于此,视之为宗尚目标之极致,在他看来,要写出“新奇”之作,关键还不在于以何者为法的问题,相反而在于如何突破前人固有的“格式”,如曰:“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15]换言之,其无非落实在了如他所主张的“信心而出,信口而谈”[16]的抒写原则。是以此处袁宏道对宋代诗文的标誉,与其说是为了重新确立可以循依的取法对象,还不如说是针对以复古派为代表的“近代文人”反其道而行之,意在破除为他们所建置的诗文复古的宗尚系统,或可以说,其“破”的企图大于其“立”的用意。
应该看到,对宋代诗文尤其是宋诗的重新审视,也不同程度地从复古派后期阶段的一些成员及其追从者那里反映出来。如王世贞晚年撰成的《读书后》其中评欧阳修文:“欧阳之文雅浑不及韩,奇峻不及柳,而雅靓亦自胜之。记序之辞纡徐曲折,碑志之辞整暇流动,而间于过折处或少力,结束处或无归着,然如此十不一二也。”[17]此言欧阳之文较之韩、柳或有不及,然也有胜出之处,其记序碑志之辞特色尤为明显。而王世贞此前所撰《艺苑巵言》评述欧、苏之文,则以为“其流也使人畏难而好易”[18],鄙薄之意居多,前后态度相比略有变化。至于他晚年为友人慎蒙所作而人所熟知的《宋诗选序》,涉及宋诗的评说,尽管根本上未改变其早年确立的抑宋“惜格”的原则立场,认定何景明“宋人似苍老而实疏鹵,元人似秀峻而实浅俗”的评语“的然”,为“二季之定裁”,然同时以为于宋诗“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19],其抑宋的姿态不能不说有所缓和。
又如与后七子阵营关系密切、被纳入其羽翼群体之一“后五子”之列的汪道昆,万历十四年(1586)序冯惟讷《诗纪》,其中云:“愿及崦嵫末光,操《诗纪》以从事,择其可为典要者,表而出之。孰近于风,则曰绪风;孰近于雅,则曰绪雅;孰近于颂,则曰绪颂。如其无当六义而美爱可传者,亦所不废,则曰绪馀。降及輓近二代,不可谓虚无人。”[20]对于诗之“典要”择选,主张以风、雅、颂三体作为铨衡准则,同时不废“美爱可传者”,包括“輓近二代”的宋、元诗歌也应在选取之列。如此,较之前后七子大多排斥宋、元两代之作的诗歌取法路数,已大为融通。胡应麟《与顾叔时论宋元二代诗十六通》书札之八,忆及汪道昆当初嘱其选“古今诗”,所言亦可印证之:“汪司马伯玉尝属仆选古今诗,以《三百》为祖,分风、雅、颂三体隶之。凡题咏感触诸诗属之风,如太白《梦游》等作是也;纪述伦常诸诗属之雅,如少陵《北征》等作是也;赞扬功德诸诗属之颂,如退之《元和》等作是也。意亦甚新。仆时以肺病不获就绪。今司马公已不复作,言之慨然,以其旨不废宋、元。”[21]据上,汪道昆嘱咐胡应麟选诗的原则,与他在《诗纪序》中主张择取诗之“典要”的方法相合,也就是,因为重以《诗》三百风、雅、颂三体为衡量标准,自然淡化了从时代的角度分辨诗歌审美价值之差异的作法,意味着即使为复古派诸子所鄙薄的宋诗乃至元诗,凡合乎风、雅、颂之旨者,自应列入诗选以供祖法,也因此胡应麟以为汪氏所嘱,“其旨不废宋、元”。
在这方面,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李维桢,其生平和王世贞、汪道昆等人多有交往,万历十一年(1583)王世贞作《末五子篇》,将他列入其中;万历十年(1582)前后汪道昆在徽州创建白榆社,后曾招之入社。特别从李维桢的诗学主张来看,其宗唐意识还十分明显,这或许正是他和王世贞等复古派人士相合调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其《青莲馆诗序》云:“诗于唐最盛,而声调气韵类不相远。”[22]即视有唐一代为诗歌鼎盛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其《唐诗纪序》也云:“汉、魏、六朝递变其体而为唐,而唐体迄于今自如。后唐而诗衰莫如宋,有出入中晚之下;后唐而诗盛莫如明,无加于初盛之上。譬之水,《三百篇》昆仑也,汉、魏、六朝龙门积石也,唐则溟渤、尾闾矣,将安所取益乎?”这又是从诗歌发展递变的历史层面,明确以唐诗为标格,不仅指示其在诗歌史上犹如“溟渤”、“尾闾”一般的聚汇和备该之盛势,而且涉及唐、宋诗歌盛衰比较的问题,尤其所谓“后唐而诗衰莫如宋”的评判,显在唐人与宋人诗歌之间,划出了审美价值优劣相异的界线。然即便如此,李维桢在看待唐、宋诗歌审美价值之时代差异问题上并未趋向极端化,这一点,特别从他《宋元诗序》一文中可以明显看出。应该说,该篇序文论及宋、元诗歌,未完全脱却作者以为继唐诗之后宋诗乃至元诗走向衰落的有关唐、宋诗歌盛衰对比的总体判断,如曰:“诗自《三百篇》至于唐而体无不备矣,宋、元人不能别为体,而所用体又止唐人,则其逊于唐也故宜。”又谓:“就诗而论,闻之诗家云,宋人调多舛,颇能纵横,元人调差醇,觉伤局促;宋似苍老而实粗鹵,元似秀峻而实浅俗;宋好创造而失之深,元善模拟而失之庸;宋专用意而废调,元专务华而离实。宋、元人何尝不学唐,或合之,或倍之。”不过,他同时又认为于宋诗乃至元诗不可偏废,自言“比长而为诗,亦沿习尚,不以宋、元诗寓目,久之悟其非也”。在李维桢看来,“以宋、元人道宋、元事,即不敢望《雅》、《颂》,于十五《国风》者宁无一二合耶”?也就是说,“宋诗有宋风焉,元诗有元风焉,采风陈诗,而政事学术、好尚习俗、升降汙隆具在目前。故行宋、元诗者,亦孔子录十五《国风》之指也”[23]。这无异于在分辨唐、宋诗歌审美价值之时代差异的同时,指述宋诗乃至元诗的价值涵义。

晚明以来凸显的对于宋代诗文再审视倾向,它所展示的,不啻是在有宋一代诗文评断上出现的变化之势,从一定意义上看,也是其时文士圈表现在知识接受和精神诉求上要求突破原有畛域的价值观念的某种异动。可以说,晚明文坛“崇尚苏学”现象的发生,与此际反思、质疑甚至颠覆尤其自有明中叶以来为复古派成员及其追从者所主张的有关宋代诗文价值评判之动向,实相呼应,同时也透出崇尚者所执持的特定的价值取向,关于后者,我们在下文中还将展开讨论。正是处于宋代诗文重新得到审视这种特殊的文学境域,作为有宋文学大家的苏轼,成了文坛聚焦的重点目标,他的诗文之作也在人们广泛阅读与多重诠释中,其文学价值得到重新型塑,从而也更被空前突出了它们在古典诗文系统中不同凡常的典范意义。焦竑在撰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刻坡仙集抄引》中云:
古今之文,至东坡先生无馀能矣。引物连类,千转万变,而不可方物,即不可之状与甚难显之情,无不随形立肖,跃然现前者,此千古一快也。[24]
作者在《答茅孝若》书札中也曾表示,“仆观唐、宋之文,莫盛于九家,绝非近代词人比也。韩、欧、曾之于法至矣,而中未有独见,是非议论未免依傍前人。子厚习之,介甫、子由乃有窥焉,于言又有所郁渤而未畅。独长公洞览流略,于濠上、竺乾之趣贯穿驰骋,而得其精微,所谓了于心于了于口与手者,善乎其能自道也”,“至子由直谓有文章以来无如子瞻者,真千古之笃论,但未易为俗人言耳”[25]。这意味着在作者眼里,苏轼之文不仅盖过唐、宋诸家文章,而且成为古今文章之冠。如此标置,自然将苏文推向极致,若非出于作者极度的推崇心理,决不至于此。然在晚明文士中间,近似焦竑这种看法的绝非偶见,如“生平慕说苏子瞻”[26]的黄汝亨,其在《苏长公文选集注序》中云:“六经之文不可与才子文人论,而虚动之宗,冒道尽神,惟《易》为至。千载而下传其妙者,蒙庄、子瞻两人而已。子瞻之文,风行波属,秦汉以来作者第一。”[27]又陈继儒《苏长公小品叙》云:“古今文章大家以百数,语及长公,自学士大夫以至贩夫灶妇,天子太后以及重译百蛮之长,谁不知有东坡?其人已往,而其神日新,其行日益远,则古今一人而已。”[28]所谓“秦汉以来作者第一”、“古今一人”云云,于苏文的评价同样不可谓不高。
值得指出的,就苏轼诗文比较而言,其文如其自言犹若“万斛泉源”、“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29],历来多为人所称道,至于诗则或受人訾议。早者如宋人张戒,他作出的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的断言,显然将苏、黄视为诗风转劣的始作俑者,其理由是“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30]。继后的严羽重以“盛唐诸人”相标格,不满“近代诸公”“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尤对苏、黄诗风多有指责,认为“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直斥苏轼诗风导致的“殆以骂詈为诗”[31]的影响效应。在复古之士那里,基于反宋诗的诗学取向,其对包括苏轼在内的宋诗人多加贬抑。王世贞《艺苑巵言》云:“诗格变自苏、黄,固也。黄意不满苏,直欲凌其上,然故不如苏也。何者?愈巧愈拙,愈新愈陈,愈近愈远。”其于苏、黄诗风的定位,基本延续了张戒、严羽等人的论调,比较苏、黄,其虽以为黄不及苏,但并不表示对苏诗的明确认可,如他又以为:“严又云诗不必太切,余初疑此言,及读子瞻诗,如‘诗人老去’、‘孟嘉醉酒’各二联,方知严语之当。”[32]严羽《沧浪诗话·诗法》论及诗“不必太着题,不必多使事”[33],上处谓严氏言诗不必太切即指此,谓苏诗“太切”,当就其好“议论”、“用事”这一点来说的。王世贞《苏长公外纪序》评苏轼诗文的一席话更耐人寻味,如果说其中“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独苏公之作最为便爽”的评语,表明他对苏文情有独钟,那么“即其诗最号为雅变杂揉者,虽不能为吾式,而亦足为吾用”[34]的说法,则于苏诗显有微词,无异乎暗示苏氏其诗不如其文。晚明时期随着宋诗更多进入文士的阅读视野,唤起他们的接受兴趣,对于苏诗的认知也出现明显的转向,邹迪光《王懋中先生诗集序》曰:
今上万历之初年,世人谭诗必曰李、何、又曰王、李,必李、何、王、李然后为诗,不李、何、王、李非诗也。又谓此四家者,其源出于青莲、少陵氏,则又曰李、杜,必李、杜而后为诗,不李、杜非诗也。自李、杜而上,……无暇数十百家,悉置不问,而仅津津于少陵、青莲、献吉、仲默、元美、于鳞六人,此何说也?少陵、青莲笼挫百氏,包络众汇,以两家尽诗则可。李、何、王、李有专至而无全造,以四家尽诗可乎?三十年中,人持此说,謷然横议,如梦未醒。近稍稍觉悟矣,而又有为英雄欺人者,跳汉、唐而之宋曰苏子瞻,必子瞻而后为诗,不子瞻非诗也。夫长公言语妙天下,其为文章吾不敢轻訾,至于诗,全是宋人窠臼,而欲以子瞻为尽诗,可乎?后进之士惑溺其说,狂趋乱走,动逾矩矱,以是求诗,诗乌得不日远?[35]
据上序,邹氏本人既不满于世人谈诗追从李、何、王、李诸子的风气,也不满于继后转向必以苏诗为是的变化迹象,除开这一点,同时引人注意,则是他观察到的,自万历之初以来三十年这一段时间,出现在诗坛从“必李、何、王、李然后为诗”转至“必子瞻而后为诗”的变易之动向。另一方面,邹氏自言不敢“轻訾”苏文,然谓苏诗“全是宋人窠臼”,其也传递出苏诗不及苏文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对此,谭元春则不以为然,他在《东坡诗选序》中指出,“人之言曰:‘东坡诗不如文。文通而诗窒,文空而诗积,文净而诗芜,文千变不穷,而诗固一法,足以泥人。’夫如是,是其诗岂特不如其文而已也?虽然,有东坡之文,亦可以不为诗,然有东坡之文而不得不见于诗者,势也。诗或以文为委,文或以诗为委,问其原何如耳。东坡之诗,则其文之委也”。并且认为,“唯东坡知诗文之所以异,唯东坡知其异而异之,而几于累其同。则文中所不用者,诗有时乎或用,文中所有馀于味者,或有时不足于诗。亦似东坡之欲其如是,而后之人不必深求者也”[36]。这是说,比较苏轼诗文,二者虽不相同,然各有特点,所以如此,乃苏氏“知诗文之所以异”而“异之”,并非因为自身诗力不足。这既是在陈述苏诗值得编选的理由,也是在驳正苏轼“诗不如文”的成见。当然,相比起来,陶望龄说苏诗“贯穴万卷,妙有罏冶,用之盈牍,而韵致愈饶”[37],又谓自己“初读苏诗,以为少陵之后一人而已;再读,更谓过之”[38],袁宏道甚至以为“苏公诗无一字不佳者”[39],其即使不能说全然言过其实,也难免偏颇之嫌,似乎非如此不足以形容苏诗“有天地来,一人而已”[40]的奇特,这又不可不谓是在“崇尚苏学”心理驱使下走向的一个极端。

二、宏博、奇诡、率意:对苏轼诗文多面的审美观照
苏轼诗文在晚明时期的流行,尤其是因为“议论”、“用事”或受前人訾议的苏诗也间获推崇,无疑成为此际文坛令人瞩目的一道景观。由此引出的问题是,苏轼诗文何以在这一时期赢得文士圈如此的青睐,它们究竟在怎样的层面上应合了晚明士人的精神需求和文学趣尚?就苏文而言,有研究者指出,有明一代苏文选本的推出,包括晚明时期各种选本的涌现,与具有功利目的的举业取向关系密切,意在便于士人习得八股制艺文字的写作,为其提供进身之阶[41]。所谓“多采择以裨公车言”[42]的苏文与举业的密切关系固然存在,考察有明一代苏文选辑层出的现象的确无法忽略这一客观情状,不过,苏轼在晚明时期备受推崇,他的诗文作品不断引发士人阅读、诠释的兴趣并得以大量刊行,这一特殊现象的发生,则绝不是由于苏文与举业之间构成的功利关系起了主导性的作用。
首先可以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乃不少晚明之士出于慕尚苏轼的心理,或相比拟,或相引重,多从其品格文章中去发掘与体验彼此精神上的共通。如“公安三袁”的袁宗道,生平“酷爱白、苏二公,而嗜长公尤甚”,以至“每下直,辄焚香静坐,命小奴伸纸,书二公闲适诗,或小文,或诗馀一二幅,倦则手一编而卧,皆山林会心语,近懒近放者也”[43]。不啻如此,“而所居之室,必以‘白苏’名”,“室虽易,而其名不改,其尚友乐天、子瞻之意,固有不能一刻忘者”[44]。又如袁中道,曾为撰次苏轼先后事,谈及个中的意图,以为“子瞻本传所载者,皆其立朝大节。然观人者,其神情正在颦笑无心之际”,于是“取其散见者,都为一本。使其老少行踪,一览便尽云耳。片甲一毛,或犹见于他书者,今未必尽收”,重于记述苏氏生平“潇洒之趣”[45]。又他在《龙湖遗墨小序》中则将李贽比作“今之子瞻”,谓贽“才与趣不及子瞻,而识力胆力,不啻过之。其性无忮害处,大约与子瞻等”[46]。其中对苏氏许重之意,也由是可见一斑。与“公安三袁”相友善的雷思霈,曾序袁宏道《潇碧堂集》,序中认为“石公胸中无尘土气,慷慨大略,以玩世涉世,以出世经世,姱节高标,超然物外。而泾渭分明,当机沉定,有香山、眉山之风”[47],曾可前序袁宏道《瓶花斋集》,指出“眉山长公,嘻笑怒骂,无非文章。石公妙得此解,随所耳目,俱可书诵”[48],则皆将袁氏为人之性行及为文之风格,更多与苏轼联系起来。再如李贽,称“苏长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自己“时一披阅,心事宛然,如对长公披襟面语”[49],或曰“心实爱此公,是以开卷便如与之面叙也”[50],更像是视苏轼为可以交心的前代知己;其《书苏文忠公外纪后》又谓“余老且拙,自度无以表见于世,势必有长公者然后可托以不朽”,于是将友人焦竑视为“今之长公”,声言“天下士愿藉弱侯以为重久矣”[51],可说是借苏轼之品望来标表其友。凡此表明,在不少晚明之士的心目中,苏轼的品格文章俨然成为特立世间、延亘绵远的某种精神象征,他们从自我或他者身上,勉力去感知这位历史人物不同寻常的召唤力,体悟彼此心神相应的精神交汇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轼给晚明士人带来的,更多是切合他们心灵深处一种独一无二的精神资源。而这一点,也特别表现在他们对苏轼诗文不同层面的体味和解读上。
激发晚明文士圈对于苏轼诗文浓烈兴趣的,首先是在他们看来从苏氏之作流溢出来的宏博和奇诡的抒写风格。还是引王世贞晚年在序《苏长公外纪》时所云:
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独苏公之作最为便爽,……苏公才甚高,蓄甚博,而出之甚达,而又甚易;凡三氏之奇尽于集,而苏公之奇不尽于集。故夫天下而有能尽苏公奇者,亿且不得一也[52]。
王世贞特别标示苏轼才识高超而凸显在苏文之中诸如“博”与“奇”的特点,自然表明其本人欣赏苏文的重要理由,同时,也似乎在指示一种时代的阅读趣味。这种阅读趣味的滋生,不能不说和作为历史上思想文化变革一个重要阶段的晚明时期相对开放、多元的文化氛围联系在一起,在根本上,它指向晚明士人在特定文化氛围之下趋向活跃、自在、丰富的精神世界,以及作为其重要表征而呈示在知识接受上更趋开博、益求奇颖的新特点。在这方面,苏氏诗文正可谓切合这种时代的阅读趣味、知识接受要求及支撑其中的精神诉求。就此,如焦竑《刻苏长公集序》也指出,苏文“神奇出之浅易,纤秾寓于澹泊,读者人人以为己之所欲言,而人人之所不能言也。才美学识,方为吾用之不暇,微独不为病而已。盖其心游乎六通四辟之途,标的不立,而物无留镞焉。迨感有众至,文动形生,役使万景而靡所穷尽,非形生有异,使形者异也”[53]。其无非认为,苏文既有他人“所不能言”之奇拔,又有游心通途、“役使万景”之博敏。而焦氏《东坡二妙题词》针对苏轼文风的一番评述,同样透露着相关的信息,如他以为“坡公之妙”,不尽在“论策序记之文”,“其流为骈语、佛偈、稗杂、谐谑,莫不矢口霏玉,动墨散珠”,“盖公天才飚发,学海渊泓,而机锋游戏,得之禅悦,凡不可摹之状与甚难显之情,一入坡手,无不跃然”,于是“模山范水,随物肖形,据案占辞,百封各意”,“嬉笑怒骂,无非文章,巷语街谈,尽成风雅矣”[54]。这不仅是说,苏轼才力不凡,学识渊深,善于描摹成文,也是说,苏文抒写因此显得博洽而新奇,触处皆是,出手非凡,不拘于为文之常格。与此相关,赵用贤《刻东坡先生志林小叙》品评苏氏“皆纪元祐、绍圣二十年中所身历事”之笔记文《志林》,则认为“其间或名宦勋业,或治朝政教,或地理方域,或梦幻幽怪,或神仙伎术,片语单词,谐谑纵浪,无不毕具,而其生平迁谪流离之苦,颠危困厄之状,亦既略备”[55]。假若说以上评语多含称誉之词,那么显然还主要是就《志林》一书记述博杂、奇致纷出、情状毕具的特点来讲的。
其实不仅是苏文,此际一些文士涉及苏诗的论评,也特别注意显现其中的出奇善变的抒写风格。如声称“苏公诗无一字不佳者”的袁宏道,曾将苏诗和李白、杜甫诗作比较,在《与李龙湖》中提出“苏公诗高古不如老杜,而超脱变怪过之,有天地来,一人而已”[56];在《答梅客生开府》中又对比李、杜诗歌,以为“苏公之诗,出世入世,粗言细语,总归玄奥,怳惚变怪,无非情实”[57]。有关苏诗与李、杜诗的联系,苏辙就曾以为,苏诗“本似李、杜”[58],而于杜诗尤多习之,苏氏本人称“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59],可见其于杜诗之倾心。王世贞撰于晚年的《书苏诗后》,谈及苏诗和杜诗的问题,指出苏氏“见夫盛唐之诗格极高、调极美而不能,多有不足以酬物而尽变,故独于少陵氏而有合焉”,虽然王世贞也肯定苏诗于杜诗“当其所合作,亦自有斐然而不可掩”,但由于重以杜甫乃至“盛唐之诗”格调相铨衡,因此他同时又直言,“所以弗获如少陵者,才有馀而不能制其横,气有馀而不能汰其浊;角韵则险而不求妥,斗事则逞而不避粗,所谓武库中器,利钝森然”[60]。这是说,苏诗虽习学杜诗而终究突破杜甫的诗格,流于逞才使气、粗豪诡异之弊,故不及杜诗。比较起来,袁宏道则认为苏诗对于杜甫乃至李白诗歌的变异,正是其突出之处,显然,对比杜诗之“高古”,他更欣赏苏诗之“超脱变怪”;在其看来,苏诗这一善于奇变的风格特征,既超越了“唯一于虚,故目前每有遗景”[61]的李白,又胜过“唯一于实,故其诗能人而不能天,能大能化而不能神”的杜甫,甚至也因此立于自古以来独一无二的境地。

从另一方面来看,晚明士人接受苏轼诗文兴趣的激发,又多得之于特别是表现在苏氏文章中率意而出、灵动自如的抒写风格。毫无疑问,苏轼生平自评其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62],其既指涉关于文章抒写的一种理想的审美要求,也即近于评谢举廉之文所云,“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63],同时,又是对一己之文臻于这一理想之境所作的自我评价。无论如何,一种率意为之、行止自由、脱却定式的文章表现之道,显然是苏轼本人孜孜以求的。晚明文士圈对于苏文的表彰,多关涉于此。黄汝亨《苏长公文选集注序》云:
佛印师有言,子瞻胸中有万卷书,下笔无一点尘气。夫惟以万卷之贮,而行无一点尘气之笔,故无者可有,有者可无,多者能少,少者能多;随性效灵,驱役千古,如淮阴之将兵,邓林之伐材,恣其所取,纵横左右,无所不宜。故按于事而后知使事之妙,解于书而后知用书之妙。览天地知圜方,历山川知纡曲。学者诵习子瞻,而不知其学问所贮,神智所繇,益与搏虚蹑影何异?岂惟不解实事,并其所谓虚动之妙,亦未解也。
据黄氏所见,苏文多有其“妙”,甚至因是成“秦、汉以来作者第一”,且为“异代同宝”[64],离不开其本人“学问”的积贮与“神智”的驱使,故能“随性效灵,驱役千古”,无所拘牵,一任己意出之,纵横自如。看得出来,序者企图解释苏文之能恣意为之所拥有的知识底蕴和个人才智,与此同时,也表达他对苏文这样一种超卓抒写风格的倾赏之心。再看袁宏道《识雪照澄卷末》所云:
坡公作文如舞女走竿,如市儿弄丸,横心所出,腕无不受者。公尝评道子画,谓如以灯取影,横见侧出,逆来顺往,各相乘除。余谓公文亦然。其至者如晴空鸟迹,如水面风痕,有天地来,一人而已。而其说禅说道理处,往往以作意失之,所谓吴兴小儿,语语便态出,他文无是也。”[65]
袁氏在褒扬苏文之际,也一语道破其间或“说禅说道理”的“作意”之失,而这一点在他看来,实系苏文未能脱尽宋人习气所致,如他在《德山麈谭》中又云:“东坡诸作,圆活精妙,千古无匹。惟说道理,评人物,脱不得宋人气味。”[66]但认为除此,苏文尚不缺乏“横心所出”之作。至于苏文何为“作意”,何为“横心”,袁宏道乃分别举苏轼前后《赤壁赋》为例加以说明,他以为:“前赋为禅法道理所障,如老学究着深衣,通体是板。后赋直平叙去,有无量光景,只似人家小集,偶尔饤饾,欢笑自发,比特地排当者其乐十倍。至末一段,即子瞻亦不知其所以妙,语言道绝,默契而已。”[67]于二赋的取舍之意,显而易见。由袁宏道对苏文得失的指点不难见出,引发他对苏文另眼相看的,无外乎是凸显其中率意所成、无由造作、挥洒自如的抒写之笔调,其犹如“晴空鸟迹”和“水面风痕”,自然而作,灵动而出,这显然相对合乎袁宏道所强调的“信心而出,信口而谈”的抒写原则。可以想见,对于力主这一抒写原则的他来说,自然更愿意去体味苏文“横心所出”的独特意趣,更容易去演绎与之有着某种审美共识的表现风格。就此而言,袁中道在《答蔡观察元履》中为人熟知的一段陈述,可与袁宏道上述之言互相参照,其曰,“近阅陶周望祭酒集,选者以文家三尺绳之,皆其庄严整栗之撰,而尽去其有风韵者。不知率尔无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传者托不必传者以传,以不必传者易于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68]!联系前后文意,其之所以将苏文区分为“小文小说”和“高文大册”而属意前者,主要还不是因为二者比较起来“小文小说”体制相对短小的缘故,而在于这些“小文小说”多为作者“率尔无意”所出,往往有“神情”寄寓其中,不同于刻意为之的“庄严整栗”之作,因而令人爱之。由是,这里袁中道对于苏氏“率尔无意”的“小文小说”的表彰,实近乎袁宏道重苏文“横心”而非“作意”所出之意。
可以说,无论是倾心苏轼诗文宏博和奇诡的风致,还是以“随性效灵”或“横心所出”看待尤其是显示在苏文中率意而出、灵动自如的情韵,从根性上究之,乃和晚明时期趋于相对开放、多元的文化氛围相联结,实不同层面折射出这一时期在士人中间逐渐扩张开来的注重自我或个性表现的价值取向。在明代历史上,晚明社会以其思想文化的剧烈异动和裂变而为人所瞩目,这种异动和裂变在士人精神归向上具体之显著表现,即是极力标立适于自我的特立独行,专注一己之性情的表达。如李贽自言“其心狂痴,其行率易”[69],袁宏道秉持以“率心而行”[70]、“任性而发”[71]为尚的主观立场,自是典型之例。正是在这种重自我或个性表现的时代精神诉求主导下,苏轼诗文的审美价值为一些晚明之士重新发掘并不同程度加以放大,苏氏凸显在其诗文中的一己之学识、才智、性情,以及由此呈现出的宏博奇诡与率意自然的抒写风格,更与他们的主观需求相契合,也因此被目之为“横口所发,皆为文章;肆笔而书,无非道妙”[72]这样一种更能表现自我心智与性情的文学书写之范式。

三、超旷闲适之致的抉发与苏轼诗文的另面品读
如前所述,晚明士人对待苏轼这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更多将其视作切合他们心灵深处的一种独特的精神资源,围绕苏轼诗文所展开的不同层面的体味和解读,也成为他们分享这份精神资源的具体表征。只是应该看到,基于不同的精神诉求及其相关的文学趣味,晚明士人对于苏轼诗文的接受,事实上也呈示较为复杂的取向。
茅坤之子茅维,曾在作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宋苏文忠公全集叙》中评苏轼之文云,“若无意而意合,若无法而法随,其亢不迫,其隐无讳,澹而腴,浅而蓄,奇不诡于正,激不乖于和,虚者有实功,泛者有专诣,殆无位而摅隆中之抱,无史而毕龙门之长,至乃羁愁濒死之际,而居然乐香山之适,享黔娄之康,偕柴桑之隐也者,岂文士能乎哉”[73]!他在总述苏文为一般文士所不及的特点时,不忘说明苏轼虽曾处于“羁愁濒死”的境地,却在文中表现了“乐香山之适,享黔娄之康,偕柴桑之隐”的超旷与闲适,这似被认为是苏轼为人和为文中应该大书特书的一笔,也更是人所不及的卓异之处。的确,苏轼一生经历坎坷,几度起落,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发生的文学史上闻名的“乌台诗案”,成为他人生之旅的一个重大转捩点,相继贬居黄州、惠州、儋州的遭遇,使他陷入常人难以承受的困厄之境。但与其起落分明、屡遭贬黜的经历相比,人们更多注意到的,则是苏轼面对荣辱穷达而表现出的独异的人生态度。特别是其身陷困境,然曰“绝境天为破”、“澹然无忧乐”[74],又曰“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75],可谓身入绝境而心超出之,持守主观勉力化解人生苦难之立场。故被看作“超越或扬弃个人的悲哀”[76],也被看作在根本上,缘自于对儒家入世进取和达兼穷独、用行舍藏,以及佛家出世和道家遁世基本精神的融会贯通[77]。固然,苏轼秉持的这一立场,蕴含对于人生意义的自我判断,也体现了一种生存的智慧或策略,但显然,它同时又着眼于个人与现实世界之间矛盾的调和或消解,以超旷与闲适的姿态摆脱一切苦难的侵扰,以化解的睿思淡却抗争的意识。这也是苏轼诗文在历代流演而受到传统文士不断诠释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观晚明士人对于苏轼诗文的接受取向,苏氏面向人生荣辱穷达而表现出的这种超然之心、顺适之态,也成为他们品论的一个重要主题。如张大复《苏长公编年集小序》曰:
自有宇宙而有三教圣人之书,学者各守其说,莫肯相下,然其究多有阳挤而阴用之者,于是乎五脏六腑之情争扰于门户,役役焉至老死而不得休息,曰吾师故常云尔。而眉山公独能以圆神方致之用,游戏翰墨,谈笑之间,玉堂瘴海,无不等观,生老病死,视如聚沫,盖古今一人而已矣。[78]
钱谦益为张氏所撰墓志,称“君之为古文,曲折倾写,有得于苏长公,而取法于同县归熙甫”,又忆其曾谓“庄生、苏长公而后,书之可读可传者,罗贯中《水浒传》、汤若士《牡丹亭》也”[79],张氏在上序中也说自己于苏轼“自幼好读其书,多所纂集,废视以来犹能忆其什九”,又为次编年集,其慕苏之意可见一端。而据序言,苏轼以文谐戏,尤其是超然面对穷达甚至生死的态度,显然最为张氏所倾重,被许为“古今一人”,其著可与三教之书并存,这也是其编次苏集的缘起,故用他的话来说,主要的意图在于“以与三教圣人之书并存不朽,俾后之知书者有以适其性命之情”。

由张大复慕尚苏轼诗文的心向和编次苏集的旨意推求开去,则还可以特别注意这一时期编纂的《东坡禅喜集》和《东坡养生集》两部苏氏选本。
《东坡禅喜集》辑自华亭徐益孙,“取苏轼谈禅之文,汇集成编”,同邑唐文献序而刻之,继后凌濛初“以其未备,更为增订”[80]。又据凌濛初天启元年(1621)所作跋文,万历三十一年(1603)冯梦桢有吴阊之游,招凌濛初同往,联舟以行,凌以是编相示,冯遂为“点阅”[81]。唐文献在《跋东坡禅喜集后》中述及苏轼和佛学的关联时表示:
子瞻平生熟于荀、孟、孙、吴,晚遇贬谪,落落穷乡,遂以内典为摈愁捐痛之物,浸淫久之,斐然有得。唐有香山,宋有子瞻,其风流往往相类,而其借禅以为文章,二公亦差去不远。香山云外以儒行修其身,内以释教汰其心,旁以琴酒、山水、诗歌乐其志,则分明一眉山之老人而已。子瞻于生死二字虽不能与维摩、庞蕴争一线,然其谭笑轻安,坦然而化,如其为文章,则餔禅之糟,而因茹其华者多也。[82]
苏轼生平于佛学显有浸染,苏辙所撰墓志记云,“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愽辨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83]。苏轼《黄州安国寺记》也自述元丰三年(1080)谪至黄州后,“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思想“归诚佛僧,求一洗之”,于是得城南安国寺,“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84]。尤自贬谪黄州之后,苏轼对佛学的兴趣逐渐浓厚,后谪居惠州、儋州,习染佛学愈益趋深[85]。如其作于贬谪惠州后的《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即慨叹年老而欲得“数年之暇,托于佛僧之宇,尽发其书,以无所思心会如来意,庶几于无所得故而得者”,“而州之僧舍无所谓经藏者,独榜其所居室曰思无邪斋,而铭之致其志焉”[86]。《思无邪斋铭》叙曰,“东坡居士问法于子由,子由报以佛语,曰‘本觉必明,无明明觉。’居士欣然有得于孔子之言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于是幅巾危坐,终日不言,明目直视,而无所见,摄心正念,而无所觉”[87]。数度贬黜而导致的人生逆折,显然是苏轼染佛渐深不可忽视的原因,在广阔的佛海之中寻求人生苦难的超脱、自我心灵的安顿,应是他委心于此的基本取向。上引唐氏跋文,认为苏轼自遭遇贬谪以来浸濡佛学,意在“摈愁捐痛”,乃昭彰了苏氏转向习佛的主要因由,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以“谭笑轻安,坦然而化”来形容苏氏超脱安闲的人生姿态,不仅是对他习佛所臻之境的高度评鉴,而且实际上也是对《东坡禅喜集》编辑及刊行意义的某种阐释。
与上书可以并置相论的则是《东坡养生集》,编者王如锡于苏集“广搜众刻,自诗文钜牍至简尺填词,以及小言别集,凡有关于养生者悉采焉”[88],全书共分为饮食、方药、居上、游览、服御、翰墨、达观、妙理、调摄、利济、述古、志异十二门类。苏轼生平习佛之外,也濡染道家身心摄养之术,其《问养生》曰,“余问养生于吴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者顺。外轻内顺,而生理备矣”[89]。其《养生诀》又言,“近年颇留意养生。读书、延问方士多矣,其法百数,择其简易可行者,间或为之,辄有奇验。今此闲放益究其妙,乃知神仙长生非虚语尔”[90]。从苏氏对养生之道的留意,实可见出超离尘俗、安养自全的一份旷适与淡漠,这当中又多和他数罹蹇厄的特殊经历不无关联,可说是“大抵患难中有托而逃”[91]。晚明盛宾为《东坡养生集》所作序文,也谓“然则流离迁徙多方厄公(指苏轼)者,正公所以厚自养炼、借为证道之资者也”[92],即将苏轼贬谪流迁的经历和他着意养炼的行为联系起来,明其厚自养生之缘起及参证悟道之资本。有关纂辑《东坡养生集》一书的本旨,编者王如锡在序中述之颇详,引人注意:
夫东坡之集,无所不有,读者亦无所不取焉,而余独概之以养生,不几诞与?夫拟之于纵横诸家,从其文章而为言者也;约之以养生之旨,从其性情而为言者也。是故肆出而为趣,旁溢而为韵;凝特而为胆识,挺持而为节义。俶傥踔绝,一无所回疚,莫不咨嗟叹赏,谓为不可及。而不知其所以不可及,要有翛然自得,超然境遇之中,飘然埃壒之外者,乃能历生死患难而不惊,杂谐谑嬉游而不乱。故尝捧其篇章而想其丰仪,揽其遗迹而标其兴寄,思其话言而窥其洞览流略之指、悬解默喻之神。至今坡老风流依然未散,而高颧深髯、戴笠蹑屐、把盏挥毫、嘻笑怒骂之态,犹栩栩焉,奕奕焉,往来于江山湖海之上。此中不有长生久驻者存耶?……则凡世所见穷通、得丧、妍媸、纤巨,东坡既已冥而一之矣,是养生之旨也。[93]
王序以为,苏轼于养生的投注,由其性情而显,故曰“约之以养生之旨,从其性情而为言者也”,因为善自养炼,遂有一己性情“翛然自得”的调养之获,也鉴于此,人世间一切穷达得失、美丑巨细,被泯却了彼此间的客观区别,无不可等而视之。如此,正所谓是“超然境遇之中,飘然埃壒之外”,纵使面向生死厄难,也能一以超而出之,不为所困。可以说,这番论议既是对苏轼养生所得的评述,也是对编辑此集以品赏和传扬苏氏诗文“养生之旨”之意愿的概括。在这方面,又可注意王季重针对苏轼“刻刻作生计”养生之道所作的解释,他在《东坡养生集序》中谓苏氏:“无论其参悟济度,功贯三才,解脱明通,道包万有,即最纤之事,饮有饮法,食有食法,睡有睡法,行游消遣有行游消遣之法,土宜调适,不燥不濡,火候守中,亦文亦武,尊其生而养之者,老髯亦无所不用其极矣。是故有嬉笑而无怒骂,有感慨而无哀伤,有疏旷而无偪窄,有把柄而无震荡,有顺受而无逆施,烧猪熟烂,剔齿亦佳,柱杖随投,曳脚俱妙,所谓无入而不自得者也。此之谓能养生。”[94]在王季重看来,对于养生苏轼不仅无所不及,即使连日常行止起居“最纤之事”,一本于养生之法,并且善于摄养,“无入而不自得”。唯其养炼之中无不自得,故能不以哀怒为怀,处之以疏旷,受之以顺应。要而言之,这还是由苏轼诗文表露出来的超然自适的心境,追究其和苏氏本人重于养生的内在联系。
应该说,对凸显在苏轼诗文里这样一种超旷与闲适之致的关注,反映了晚明文士圈中另一面的阅读趣味,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另一面的精神归向。究其所以,尽管伴随晚明时期相对开放、多元文化氛围的形成,相较于传统,此际士人精神世界发生的剧烈的震荡,重视自我或个性表现这种激进的价值取向趋于扩张,此已是学人在晚明思想文化研究领域多所注意到的历史事实,无需赘言。然而,这一切并不代表传统的根性在士人文化性格中全然消去,特别在面向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之关系问题上,如果说,秉持重自我或个性表现之激进价值取向,难免突出二者之间的矛盾,那么,超离尘俗,逍遥容与,出入佛道,意在调和、消解二者之间的矛盾,也成为一些晚明士人倾向的生存决策,其多少表明他们文化性格的两面性。试以在晚明士人中颇具典型意义的袁宏道为例,宏道早年受禅宗影响颇深,其自言“弱冠即留意禅宗”[95],后致友人张献翼书札也言:“仆自知诗文一字不通,唯禅宗一事,不敢多让。”[96]万历二十五年(1597),其在《冯秀才其盛》一书中又表示:“割尘网,升仙毂,出宦牢,生佛家,此是尘沙第一佳趣。”[97]说明他早年已濡染佛学尤其是禅宗,以后又萌生超世离俗、修性戒行的心念。万历二十七年(1599),袁宏道“述古德要语,附以己见”,勒成《西方合论》一书,此被袁宗道看成是“箴狂禅而作也”[98],其自谓:“余十年学道,堕此狂病,后因触机,薄有省发。遂简尘劳,归心净土,取龙树、天台、智者、永明等论,细心披读,忽尔疑豁。”[99]因而这一年也被认作是袁氏佛学态度发生显著变化的分界线,即由早先重于禅宗悟觉,归向重于修持的净土。这也如袁中道为宏道所撰行状所述,以为自此年起,“先生之学复稍稍变,觉龙湖等所见,尚欠稳实。以为悟修犹两毂也,向者所见,偏重悟理,而尽废修持,遗弃伦物,偭背绳墨,纵放习气,亦是膏肓之病”,“遂一矫而主修,自律甚严,自检甚密,以澹守之,以静凝之”[100]。虽主要就其佛学取向而言,然从中也可看出袁宏道人生态度的明显转向,即由早年率性之“狂”,趋主超俗之“澹”之“静”,其严于律戒、顺适淡冷的退守意识,由是分明可见。这一点也多少从他的文学意趣中逗漏出来,最能说明问题的,还属其《叙呙氏家绳集》所言:“苏子瞻酷嗜陶令诗,贵其淡而适也。凡物酿之得甘,灸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浓者不复薄,甘者不复辛,唯淡也无不可造;无不可造,是文之真变态也。风值水而漪生,日薄山而岚出,虽有顾、吴,不能设色也,淡之至也。元亮以之。东野、长江欲以人力取淡,刻露之极,遂成寒瘦。香山之率也,玉局之放也,而一累于理,一累于学,故皆望岫焉而却,其才非不至也,非淡之本色也。”[101]是处所谓文之“淡”,实具两重涵义,一是指自然之意,故谓其不可造作,与“人力”所为、“刻露”所示相对;一是指闲淡之意,故以陶诗比拟,又与“率”、“放”之作相区分。如果说,前者尚显出其和袁宏道原先“信心而出,信口而谈”这一重“性灵”发抒之论的联系,那么,后者则当是“以澹守之,以静凝之”意识主导下以闲适淡泊为尚文学意趣的流露。值得指出的是,叙言以苏轼偏嗜陶诗相标,也无非示意作者和苏氏诗趣之合调。
总之,苏轼诗文表现出的超然之心和顺适之态,在指向一种生存的智慧或策略的同时,也提示了尤其是作者面向人生困境而以调适乃至消释现实矛盾为旨归的一种淡退心向。晚明文士圈在接受苏轼诗文之际特别是对于凸显其中的超旷与闲适之致的品论和推重,反映出其文学趣味的另一极,在深层次上,苏轼诗文中的这种超豁而非执固、淡宕而非激亢的人格特征及独特意致,正应合了一些晚明之士基于其文化根性的一种勉力协调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关系的生存取向,一种有异于重自我或个性表现之激进姿态的退守意识。其称道苏轼其人其作所谓“玉堂瘴海,无不等观,生老病死,视如聚沫”也好,所谓“翛然自得”,以至“超然境遇之中,飘然埃壒之外”也罢,无不指示了这一特点。至于如袁宏道拈出苏氏于陶诗“贵其淡而适”的偏嗜以及对于“淡”之本色的诠释,如结合其“遂简尘劳,归心净土”的佛学取向乃至人生态度的转向观之,则更成为可以说明此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

结 语
综观苏轼诗文在晚明文坛的流行趋势,其与这一时期宋代诗文受到重新审视的文学境域形成不可分割的联系,它反映了同晚明士人趋于相对开放、活跃的知识接受及精神诉求相应合的阅读视界的某种扩展。对于此际众多的文人学士而言,苏轼的品格文章,被他们视为与其心灵世界颇相契合的一份独一无二的精神资源,乃极力予以表彰,与此同时,藉由人们的广泛阅读与多重诠释,苏轼诗文的文学审美价值得以重新型塑,尤其是对于向来多受到訾议的苏诗的认知,也出现明显的转向,是以它们在古典诗文系统的典范意义进一步为之凸显。从具体的接受态势观之,苏轼诗文以其独异的抒写风格,在一定意义上切合了晚明士人不同层面的精神诉求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文学趣味。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他们推重苏氏之作流溢出的诸如宏博、奇诡及率意而出的风调;另一方面,又偏尚呈示其中的超旷与闲适的意致。这种多重的接受取向,归根结底,与晚明士人既重自我或个性表现而又未全然脱却传统文化根性的特定的精神归向相构联,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晚明士人文化性格及其表现在价值取向上的激进与退守相交织的复杂性。有鉴于此,对于苏轼诗文的接受,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晚明时代精神和阅读趣味的一个缩影。
[①]《苏长公外纪序》,《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十二,明刊本。
[②]《徐孟孺》,《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八十二。
[③]《焦氏澹园续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万历刊本,集部第136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④]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曾述及包括晚明之士在内的明代苏文诸选家,参见该书第4页、第9页至10页,台湾大安出版社1988年版。
[⑤]仅据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巴蜀书社1990年版)载录,万历至崇祯年间刊行的各类苏轼诗文选评本主要有:谭元春选《东坡诗选》十四卷,陈仁锡评《东坡先生诗集》三十二卷,茅坤等评《苏文》六卷,归有光编、倪元璐评《宋大家苏文忠公文选》九卷,李贽选《坡仙集》十六卷、钟惺选评《东坡文选》二十卷,陈仁锡选评《苏文奇赏》五十卷,陈绍英辑《苏长公文燧》,詹兆圣选评《苏长公密语》十六卷,王纳谏选评《苏长公小品》四卷,郑圭辑《苏长公合作》,王世贞辑《苏长公外纪》五卷,茅坤、钟惺评《苏文忠公策论选》十二卷,《东坡尺牍》五卷,《苏长公二妙集》二十二卷,《苏长公表启》五卷,冯梦桢批点、凌濛初辑《东坡禅喜集》十四卷,王如锡编《东坡养生集》十二卷,朱之蕃辑《新刻苏长公诗文选胜》六卷,陈于廷编《苏长公文腴》三十卷、《诗腴》八卷,袁宏道、钟惺辑《东坡诗文选》,《宋苏文忠公居儋录》五卷,《宋苏文忠公海外集》四卷,《寓惠录》四卷,王同轨编《苏公寓黄录》二卷,阎士选评释《苏文忠公胶西集》四卷,崔邦亮选《苏文忠公集选》三十卷,钱士鳌选《苏长公集选》二十二卷,陈梦槐选《东坡集选》五十卷等。
[⑥]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卷十一,中册,第497页至4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⑦]同上书卷十,上册,第458页。
[⑧]同上书卷二十四,下册,第1029页。
[⑨]《答秦中罗解元》,同上书卷二十四,下册,第1053页。
[⑩]同上书卷十一,中册,第497页
[11]《叙梅子马王程稿》,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十八,中册,第6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2]《答陶石篑》,同上书卷二十一,中册,第743页。
[13]同上书卷十八,中册,第710页。
[14]《张幼于》卷十一,同上书,上册,第501页。
[15]《答李元善》,同上书卷二十二,中册,第786页。
[16]《张幼于》卷十一,同上书,上册,第501页。
[17]《书欧阳文后》,《读书后》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28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8]《艺苑巵言四》,《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七,明万历刊本。
[19]《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十一。
[20]《诗纪序》,《太函集》卷二十四,明万历刊本。
[21]《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290册。
[22]《大泌山房集》卷二十四,明万历刊本。
[23]同上书卷九。
[24]《坡仙集》卷首,明万历刊本。
[25]《焦氏澹园续集》卷五。
[26]熊明遇《寓林集序》,黄汝亨《寓林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天启刊本,集部第1368册。
[27]同上书卷二。
[28]《陈眉公先生全集》卷二,明崇祯刊本。
[29]《自评文》,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六十六,第五册,第2069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30]《岁寒堂诗话》卷上,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第452页、45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31]《诗辨》,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第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32]《艺苑巵言四》,《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七。
[33]《沧浪诗话校释》,第114页。
[34]《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十一。
[35]《调象庵稿》卷二十七,明万历刊本。
[36]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卷二十二,下册,第596页至4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7]《及幼草序》,《歇庵集》卷四,明万历刊本。
[38]《与袁六休》,同上书卷十一。
[39]《答梅客生开府》,《袁宏道集笺校》卷二十一,中册,第734页。
[40]袁宏道《与李龙湖》,同上书卷二十一,中册,第750页。
[41]参见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第5页至7页。
[42]陈继儒《三苏全集叙》,《陈眉公先生全集》卷二。
[43]标签组:[宋朝] [诗歌] [苏轼] [袁宏道] [续修四库全书] [袁宏道集笺校] [苏轼文集]
上一篇:《春末闲谈》批判封建
下一篇:手抄唐诗三百首之——竹里馆_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