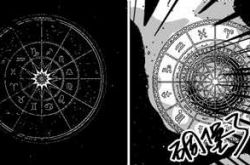发表自话题:博物馆文物喊你去蹦迪
“老成都”,有多老?
这个问题可以问雕塑艺术家朱成。在近30年的成都城市建设中,他的城建雕塑,出现在了多个地标级区域,成为“老成都的标志”,如:宽窄巷子艺术砖墙,四川美术馆馆前雕塑,都江堰的“百年民俗图像”……
 宽窄巷子·栓马桩 ·朱成
宽窄巷子·栓马桩 ·朱成
 都江堰百年民俗博物馆·朱成,这种老照片结合雕塑的作品被称他作“二维半”
都江堰百年民俗博物馆·朱成,这种老照片结合雕塑的作品被称他作“二维半”
 都江堰百年民俗博物馆·朱成
都江堰百年民俗博物馆·朱成
 四川省美术馆外 《手》· 朱成
四川省美术馆外 《手》· 朱成
成都,这座正在逐渐变新的城市里,人们榨取着与“过去”有关的一切老东西。
“老”,是外来者对成都的期待,但城市的发展速度已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本地人眼里的成都,正在逐步加热,生活速度追着房价一起上浮。2017年三月,随着“限购令”的出炉,更多人的话题,从晒太阳打麻将,换成了房子。
担心没有房子住的不止是人,“博物馆”其实也会,三个月前,“成都朱成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副馆长朱明打电话给我,说老博物馆那片区域可能真的要拆迁了。我忽然觉得,写于两年前的这篇文字,是时候发出来了。
—— (一) ——
没人能在导航地图里找到朱成石刻艺术博物馆,它挤压在成都西北,一块新楼盘围了一圈儿的城乡结合部里。走到那的时候,最先看到是一堆瓦砾,朋友指着碎砖头对我说:“这儿是个菜市场,两天前还是。”我只看见房子后面堆满废水泥,有个垃圾场。村里野孩子骑着共享单车嬉闹而过,后面跟了几条土狗,也跑的很欢。
▲ 青杠林村所在的城乡结合部景像 【图片】田坤
走过这个猪肉摊子,对面是个烧酒铺子,门前马路牙子上,白纸板立两红字:“理发”。再往前,白光光的地上竖把伞,修鞋的老头下面坐着。他屁股后面,褪了漆色的红门紧闭。朋友说:“到了。”
▲ 门口修鞋的老人 【图片】田坤
“哪?”
“这。”
“博物馆?”
我不太信,在门上找字,“旺铺出售18万”、“禁止停车”、“禁止摆摊”。旁边才有小小的几个:“景观造型艺术研究所。”
▲ 石刻博物馆 【图片】田坤
拍了拍门,里面静悄悄的。朋友说,朱老师可能吃饭去了,我们去河对岸找他。
府河,也叫郫江。从博物馆门前南下,割裂整个成都的西北郊。这边是金牛区,对岸的郫县以豆瓣酱闻名天下,现也纳入市辖,改名叫郫都区。而府河更著名的名字叫锦江,很多人能从唐诗里背诵:“锦江春色来天地。”
时逢春三月,幽壑里芭蕉叶子绿的滴水,坐在对岸的露天茶园里,看到吊桥上行人和电瓶车挤着通过,摇摇晃晃的。从这遥望博物馆,我看见了一个用钢筋和铁皮架起的空中走廊,二楼的平台向河方向伸出一块。玻璃是落地窗,远远望去闪着光。
空气里油菜花香阵阵袭来,一起来的朋友说,这地方真不错!不像个博物馆,倒像是杜甫的草堂,这里离西岭雪山也不远,老朱坐在房子里,“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画面,泡一杯茶就能品见。
听说我们是来拜访朱成,饭馆的老板娘连声说:“朱老师很好!”在老板娘的记忆里,在青杠林村,朱成比本地人更像土著。她十年前接手餐馆。那个时候朱成就是客人。很多个黄昏,打了一下午麻将的附近村民散去,就远远看到老朱摇晃晃走过吊桥,来吃饭。
老板娘指着院子里一座露台,也是钢筋和铁皮架子:朱老师喜欢上楼吃,坐在靠河的角落。站在上面,与博物馆隔桥相对,相互能望见。老朱最喜欢点的两道菜都是河鲜,干煸鳝鱼段和红烧鲫鱼,适合下酒,他却从不喝酒。
曾经是村里几个组的地方,修起了一个安置小区叫府河星城,这十年变化很大。半个青杠林村已经拆的不知所踪。老板娘的婆婆过来帮端盘子,我随口问家住哪?婆婆说住在青杠林5组。老板娘怕我没听懂,补充说:就是府河星城,老年人都改不了口……
只有博物馆是老样子,常年大门紧闭。偶尔朱成会带几个大人物来这里聊天吃饭,其中有一个她在电视里见过,是徐峥。
更多时,朱成是一人。店里打杂的阿姨忽然八卦起来,说她曾经大着胆子问过朱成:“朱老师,咋从没见你带老婆来吃饭?”
大家哄笑:“朱老师怎么说?”
“就笑一下,不说话。”
“他不跟你们开玩笑啊?”
阿姨忽然腼腆起来“朱老师人很和蔼,跟我们打招呼,不得开玩笑。他那种级别的人,开玩笑也不得跟我们这些人开噻!”
得知我们要去参观博物馆,他们也好奇:“博物馆里都有啥子?”
我惊讶“你们不晓得?这么多年没进去过?”
“没有哦,里面有一个司机跟朱老师开车,常来打牌,我们问他,可不可以带我们进去耍一下。他说可以啊。最后还是没去……里面是不是很豪华?”
我想起那面红漆斑驳的铁门和上石棉瓦天棚的破烂样子,只能笑笑。
坐一会,对岸打来电话,说朱老师回来了。我们站起身,准备过河。
—— (二) ——
敲开铁门,老朱在天棚底下朝我们摆手。他身材高大,穿着军绿色的钓鱼衫,看起来倒像只有五十多岁的样子,面孔如刀斧凿过,有力、沉默。
我向左右巡视了一眼,这里看起来就像个焊接工厂,乡镇里常见的那种。门廊狭窄,只够停两辆车。铁架子和KT板是某个大型雕塑正在完成的一部分,它们斜靠在墙上。通道上立了个石狮子,旁边一个泰山石敢当。最外层存放石刻的石棉瓦天棚,歪扭扭的,硬是把一个角塞到了通行道上。路两边都是库房,锁斜挂在门上。
我们一行四人,老张、老马二人是文博机构的考古专家,小姑娘是朱明(朱成之子)公司的助理。尽管不是第一次见老朱,她还是显得紧张,磕巴巴地跟老朱介绍我:“这是新来的编辑,想来采访一下你?”朱成很警觉:“啥子编辑?”很快又追了一句:“不接受采访,我不接受采访!你回去跟朱明说,他上次给我那个东西是啥子?根本没搞懂我意思!”
老马是朱明的发小,对老爷子的脾气摸得透,立刻接了话:“唐书记(唐良智,前成都市委书记,当时职位尚未变动)说成都要建博物馆城市,朱老师这一次可以了!”
朱成对这个信息很在意,下意识的收了收脖子,降低身高靠近我们,想听的多一点。
“ 北改朱老师晓得噻!这一片连到凤凰山那边,要做景观改造。”
“改造啥子!十年前就喊到要改造。”朱成笑笑,却有点言不由衷。
“这一次真要动了,上府河生态区,给我们文保部门都发文件了,我回去找一下发给你。”
“你找嘛!可以发给朱明。”
“最近动作大哦,发文说景观改造要我们部门要做好指导工作!我们能指导个锤子!不球懂嘛!要请朱老师你们这些专家来噻!完了市里面开会,朱老师过来指导一下。”老朱高兴了起来:“不但要指导,我还能给他们上一课!”气氛变得欢快,我们说去看看博物馆的藏品,老朱挥了下手,让院里的师傅老刘去给我们开灯。
走向朱成身后,一个石头的世界在我们眼前铺开:天棚下的石敢当、石狮子、地面上长着苔藓面容模糊的石雕野兽。昏暗的仓库里挤满了石人,石马,上千块刻满浮雕的石碑……
 博物馆藏品·图像建筑献上馆cavac提供
博物馆藏品·图像建筑献上馆cavac提供
 博物馆藏品·图像建筑献上馆cavac提供
博物馆藏品·图像建筑献上馆cavac提供
 博物馆藏品·图像建筑献上馆cavac提供
博物馆藏品·图像建筑献上馆cavac提供
 博物馆藏品·图像建筑献上馆cavac提供
博物馆藏品·图像建筑献上馆cavac提供
 博物馆藏品·图像建筑献上馆cavac提供
博物馆藏品·图像建筑献上馆cavac提供
 博物馆藏品·图像建筑献上馆cavac提供
博物馆藏品·图像建筑献上馆cavac提供
朱成的收藏,震撼人心的首先是是数量。坛子,就是上百个坛子码在一起。有些地方是人脸,各种表情的面孔挤在一起。门神是武将,一左一右对峙着。当然最多的是石刻房子,相似又不相似,有的做出了凹凸,有的则涂鸦一样只有线条。围绕着房子四周,有许多生灵:龙凤飞舞,瑞草缠绕,嗷嗷鹿鸣。还有女人,很多个女人从门里探出头来,面孔浮肿。院子里留了很多树,和棚子紧紧靠在一起。修建仓库的时候,朱成刻意地保留了这些绿色,有些就从天棚留给它们的洞里伸出头去。我从中感受到了一个艺术家的慈悲。漫步其中,二人时而感叹,时而相互询问:“有没有清明上河图的感觉?”
▲ 石刻博物馆 【图片】田坤
“是,非常世俗。这些都来自民间。”
“大型墓葬有很多,这种民间的东西,这么大的收藏量,成为一个序列,太罕见了!”
“之前想过根据年代来断代,现在看起来大多数时间可能很集中,集中在宋、明、清。”
“也有汉代的东西。”
“是的,也有。”
最后,我们不约而同想起了一个词语:“人间天国。”
震撼是一部分,问题也来的很快:“风化的很厉害。”
“四川的这种石刻,基本是红砂岩,风化起来快的很。你看这些,使点劲,就酥了。再不打整,脸都没了。”这种可惜,就不是不约而同,而是有目共睹了。
存放石刻的仓库,是由水泥预制板搭建起来的半露天建筑,昏暗的灯光里密布着蛛网一样的钢筋,它们是承重之用。靠墙的地方打了三四层槽钢,石壁抵住墙用钢圈儿卡在上面,石刻像是勋章一样被挂满了墙。存放石刻的仓库,是由水泥预制板搭建起来的半露天建筑,昏暗的灯光里密布着蛛网一样的钢筋,它们是承重之用。靠墙的地方打了三四层槽钢,石壁抵住墙用钢圈儿卡在上面,石刻像是勋章一样被挂满了墙。
尽管做了各种空间的利用和排布,仓库里依然人声马嘶,拥挤无比。因为太挤了,有些石刻挤不进墙上,只能随意的靠在地上。图案里,一把椅子立在正中,男女站在两侧,谁都想坐。还有些屋子中间,竖立着祖先的牌位,可能刻上名字,就比较安全。中国人之为人,哪怕死了,也必须要有位子,挤来挤去,立锥之地都快没了。
有座房子上画了牌楼,上面还挂块匾:“亿万斯年。”还想亿万斯年?买房也只管75年,死后房子修的好,也就几百年,就被刨出来了。在居住空间问题上,活人和死人,都不安全。另有牌位上写着:“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想必是来自“城头幻变大王旗”的军阀混战年代。
开灯的老刘忽然开腔:“朱大爷这塌塌(四川方言,地方的意思)东西,修的没得规划!东一坨,西一坨,今年弄一哈,明年弄一哈。”
我指着那槽钢问他,这怎么抬上去的?不结实吧?
“不是人工抬哦,随便一块都两三百斤。是绞索绞上去的。绞上去抵住墙,人一推,卡住,然后烧电焊。现在年代久了,还是要不得。想要真正的安全还是应该搁在地上。那些石头年月一久就风化,风化后你再搬,就彻底没有面貌了。现在搬上去的,起码七八年了。前面(槽钢)做的还好,刷过漆。后面的不刷漆,风吹雨淋的,就要朽坏。雨淋到那个石头,虽然裂缝不得好大,但是年代久了它要变形。”
我问他“现在这些库房,这些年检修没有?”
“检修啥子,你看哪个敢上去吗(石棉瓦棚)?它这个瓦承不起人。当时应该把那些树子砍了!那个雨一下,瓦上面积了很多叶子,压力很大!”
“其实就他这些东西,修一栋房子就解决了。就这块地,直接修过沟,把地下掏空。”老刘说的高兴起来:“修个五层,地下修成停车场,好漂亮哦。石刻全部放在地下, 就两边喷起,全部拿线搅。这边接待室,这边是办公室,这边卧室,还有朱大爷耍的塌塌,都够。就这么多东西,一栋房子就解决了。
最后,却是一声叹息:“没得钱,只有百十万资金,动都不敢动。”
—— (三) ——
第一次听说朱成,是一起偷窃案子。
当时有一群小偷光临了四川美术馆的大门,他们的目标并非馆藏的画作,而是门口的雕塑。这群人技巧娴熟,以宰杀动物的手法切开整个水泥基座。最后,那尊高数米、重数吨的不锈钢雕塑,脱离了母体,像一头昏睡的大象一样,被人打包带走。
小偷们识货,被盗作品叫《千钧一箭》,是朱成的代表作,世界上一共有五件,最好的一件收藏在瑞士奥利匹克博物馆。被盗走是捐赠给省美术馆的副品。
朱成这个40后出生的老人,在成都留下的痕迹不止于此:他的半浮雕作品《拴马桩》,几乎每一个去过宽窄巷子的游客相机里都有它;皇城老妈火锅店,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师保罗·安德鲁专程去与他的作品《万户千门》合影,那是一面用铸铁和陶砖铸造的墙,墙里塞着几十个翻修后的传统老门窗;在国际会展中心,他把老照片和破凳子捏成一个《老茶馆》,全国各地,都有人抄袭……
创作之外,朱成常年跟着拆房子工人的屁股,趴进灰尘,捡起骨骸——旧砖旧瓦在日渐遗失。他从拆迁老街区里捡了很多块,视若珍宝。
当然,他收藏最多的东西是墓像砖。有人告诉我,这种东西品级不高,市面上一两千块钱就能收到。我拍了照发给一些玩收藏的朋友,他们说:“这一看就不是博物馆的!不值钱啊。”值钱这个问题,在朱成那里有另外的答案:“中国古人把建筑作为一种图腾,为什么把它安放在地下,因为把它看作是另一个世界的家。”
他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给我看,说:“你说这砖头值什么钱?很值钱,也很不值钱。老建筑毁坏了,在我眼里是玉碎。玉碎的时候,我只能记录。等到需要修复,就是瓦全,那时候就能用到这些东西。”
像是要印证这一点,他带我去另外一个仓库,去看他这些年的作品。
木刻金刚经排成一面佛墙,省文物局批准成立博物馆的批复做成了喷绘,从佛墙前露出半米,剩下的塞在老家具靠背后面。
这里也有很多石刻浮雕,雕刻成廊的形状。朱成介绍说“这是一种杆栏式和斗拱式的建筑,代表着先民迁徙的历史。他们把居住过的房子刻在石头上,然后摆到墓室里去。除了保护肉身、同时也是庇护精神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就看到了巨大的脚,巨大的头颅——《喜怒哀乐》,超过三米高的树脂和木板里凸出人脸,凝视黑暗,压倒一切。
 朱成作品《喜怒哀乐》,图像建筑献上馆cavac提供
朱成作品《喜怒哀乐》,图像建筑献上馆cavac提供
▲ 朱成作品《喜怒哀乐》 【图片】田坤
▲ 《喜怒哀乐》细节 【图片】田坤
走近细看,竟发现组成这些面容的,是一些非同寻常的东西。喜是各朝各代的铜钱镶嵌出来的,怒是老麻将,哀是私章、乐是木活字。这让我联想起他在火锅店前留下的公共空间作品——《万户千门》,那一次他用的是修缮之后的老门窗。朱成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些故物续命。
院子里忽然传来老刘大呼小叫的声音,我们走出仓库,发现下雨了。老刘正在和几个工人搬动一块KT板子,朱成说那是都江堰的项目,半成品,拖了很久,钱一直都收不回来。
“还差几百万。都江堰的东西本来是都江堰在管,现在划到成都,当官的都换了,就有点麻烦。”
“新来的(官员)没有接手你这个事情。单价就又换成用平方算,啥子事情都搞焦了,找这个找那个。政府的事情麻烦得很,他不像私人的,看到要得了就结款。这个把字签了,还要那个。弄不清正的副的,要跑很多趟。”
这些年,朱成一直在做项目,这是挣钱的唯一途径。他把所有收入都砸到收藏上了,但理想中的博物馆一直遥遥无期。
“这些东西,你看了觉得多,我还觉得少。这种文物没得人留意,放在民间很快就损坏了。我是替政府收着,都不是我的,是政府的。”
想了想,他又说:“现在东西越来越难收了,要是早几年我能有一笔资金,规模还能大一倍。你看着这房子修的屁(四川方言,意思是不好),但是里面的东西都是价值连城。比如说有一万块钱,我宁肯能多收一块东西……”
跟着老朱在院子里再转一圈,才知道什么是危机四伏。博物馆靠河的一面房子快要倒了。由于选址不好,河一涨水,砖脚子打下的墙根,就要顺着柔软的沙地下沉。老刘说,现在要不是有颗老树的树根托着,墙早都塌了。
—— (四) ——
听从了朱成的指点,我去了成都的潘家园——送仙桥古玩市场。昨晚下了雨,早上光很通透,地上湿湿的,阳光碎碎的。
今天市场里比较安静,牌子比人多:原矿绿松石、银元银锭古玩铜元。我问起了墓像石,大部分人都摇摇头:“没有!”热心的行家指点我:你问的这个品级不高,又沉,没多少人玩的。你得到乡下去收!”看我锲而不舍,行家也失望,对我说:“你非要问,去那边古玩商店去问吧,国营的。”
古玩商店还真有两块,说是广安龙觉寺挖的。小的五万,大的三十万。成都古玩市场,起于九十年代,最早是在猛追湾、游泳池,再得到二仙庵,然后一路繁荣,四方开花。朱成常年活动于此。
在一位本地藏家的记忆里,朱成逛市场的气势很足,拿麻袋来,扛麻袋走,就跟买一堆萝卜似的“:……把玩着锡壶准备离开市场的时候,我突然看见朱成提着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从我身边经过。把他叫住,看看他寻了些什么宝物。哇,两麻袋全是锡壶!朱成指着我手里那把壶说:“要是你动手再晚一点,今天它肯定也装在我的麻袋里了。”
市场里,要论凶神恶煞,除了朱成,还有一位——“人生第一快事,就是逛地摊捡破烂,藏家说:舵爷,你要,就给两千元,别人来,八千不卖,这点钱,让你新做,你都做不起。我说:啰嗦,给钱。”
自述的这位,人称舵爷,是成都收藏界的另一位传奇——樊建川。
樊建川在微博上很有名,有上百万的粉丝。他从一名地产大亨,切入到收藏领域,用短短二十年时间完成了一批近现代主题的收藏。建成了“建川博物馆聚落”。成为了四川著名景点安仁古镇的招牌。朱成和樊建川关系匪浅,樊建川喜欢喊朱成“腿师”。在四川话里这个词有着“大腕”的意思。朱成也乐于在一切访谈中聊起樊建川的收藏理想,看做是自己的同类人。
今天80后、90后的年轻人,很少有不知道盗墓小说《鬼吹灯》的。这部火爆的网络小说,以北京潘家园古玩江湖为原型,复原了一个具有知青元素的江湖世界:当过兵,当过倒爷,又插过队的人物主角,带点小理想挣扎在光影迷离的九十年代。
这其实就是朱成和樊建川们的故事,朱成是老三届,文革十年,他赶上了知青下乡的开头。樊建川比朱成小十岁,赶上了下乡的尾巴。当他们下乡归来后,陷入了当时青年的一种共同状态:“文化的英雄和先知”!
经过文革十年的黑暗,焦渴的青年们对与文化有关的一切事情感兴趣。这也是促成他们加入90年代收藏热的最初动力。当时,朱成考进了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开始了民俗收藏。而下乡后又当兵的樊建川,则把红色文化和近代民俗做了自己的收藏目标。
经过九十年代的大爆发,2001年,朱成和樊建川完成了自己的首批藏品积累,入选了成都市当年成立的四大私立博物馆。到了今天,成都范围的私立博物馆已经接近一百家,成为首屈一指的博物馆之城。樊建川成为了其中的佼佼者,朱成则变成了其中的挣扎者。
在朱成的独子朱明看来,父亲的性格是促成这一现状的重要原因,比如——在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上。朱成喜欢带老外参馆,看到老外错愕惊惶的表情,他愉悦莫名。
“德国柏林现代艺术中心的汉斯到我这里来,打开库房后他半天合不上嘴,说朱成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说了一连串非常,然后就找不到词语接下去了。”
“有一伙日本人到这里来,日本人傲慢啊!从来看不起中国人,趾高气扬的德性。来了一看,哇,成千上万件!呆了几分钟,脸色铁青,一句话也不说,一件东西也没细看,就走了!他们老远来干什么啊?为什么那么快就跑了?告诉你们吧,他们受不了这个打击!这些东西他们见不得,听不得,恐怖!”
朱明,并不认可父亲的这种姿态。接受过国外教育背景的他,一直觉得博物馆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来运营,父亲的所作所为让他想起了恋物癖。
“作为博物馆的创始人,他有义务向公众解释!而不是高深莫测,玩些语言游戏。”
朱明毕业后,曾与朱成在博物馆共事了一段时间。最后的结果是“逃离惨淡的现实,逃离针锋相对的父子关系”。逃离之后的朱明开设了自己的空间设计工作室,数年摸爬滚打后,他已小有名气。一些项目开始通过他的手交接给父亲。悻悻然的老朱不知道说什么,开始称呼自己的儿子为:独行侠。
朱明说:“很多父亲都觉得自己的儿子是个巨婴,虽然我不是。”很长时间,父子关系都针锋相对。父子二人性格不同,理想不同,就连身高都不同。身材不高的朱明比起激情的父亲显得更加理性。具有留学背景的朱明身边,聚集了一批新锐的青年艺术家,他们不局限于地域,专业,彼此分享与合作,参与国际艺术项目的互动。
对博物馆,年轻人时常迸发出新想法,比如站在秦砖汉瓦中间,来场声光电音乐会什么的。但这种想法多半在空洞的文字阶段,就要被朱成严厉驳回。在博物馆这件事情上,朱明慢慢地开始理解父亲的感情,父亲曾让他读《图像中国建筑史》,这让朱明想起梁思成父子的《营造法式》,他将此看做一种精神上的传承,一种关系的隐喻。最后朱明说,我理解了父亲。
现在,朱明召集人手,进行博物馆线上平台的开发。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人参与博物馆的互动中来。现阶段怎么跟自己的父亲打交道?朱明也觉得棘手,两代人之间的沟通问题很大。
我和朱明去博物馆那天,正是清明节前,两个人说着第二天祭祖的事情就吵了起来,朱成坐在车上,面色不善,话没说清楚车就不耐烦地开走了。
我看到朱明用一路用四川话远远追着喊:“爸爸,爸爸!”快跑到路的尽头,车才在尘土里慢悠悠停了下来。
朱明现在的策略是回避碰面,先做东西——“年轻人先要做事,不能啥事都指望爸爸。他是个七十岁的老人了,你要他怎么样?”
针对博物馆文本资料的稀缺,他邀请了考古专家,准备对藏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理和资料采集。老马和老张这两位来自考古系统的专家,就是朱明计划的一部分。
来自成都博物馆的张行,在观看博物馆后迸发了极大的热情,他拟定了一份考古方案,准备以一个90天的周期,整理出一百块最具代表性的藏品资料。在方案的尾部,他写道:整理所得,在考古期刊中发表,由双方共同署名。
对此,朱明心存疑虑,他也有他的计划。整个博物馆的视觉系统,是具有商业价值和版权的。以他人名义发表,在法律上代表什么?他吃不准。
这件事暂此搁浅。
其实朱成早就识到了博物馆的瓶颈。
2002年的一段专访中,他恳切地说:“因为博物馆的运作还是一件很难的事,这么多年来我搜集了很多这种资料,建立起它,对我最难的一件事就是它需要很大的资金,这事情本身是一个社会的事情,靠我个人的力量做到现在这步好像已经做到最后一步,已经做到顶点了,要靠个人的力量已经无法完成了。那么现在我也通过海外媒体、国内的朋友,求助于社会、求助于政府,来一起完成这个事情。”
朱明对此很愤怒,“不应该这样子!在国外,早都有社会力量涌入了,在中国,任何事情就一个问题!级别嘛!”朱明的愤懑并非没有道理,至今,针对民间私立博物馆的一系列匹配政策,都还停留在国家级的口头鼓励阶段,在地方政府层面,根本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出台。甚至连水电费、税费这样一些基本的减免都没有配套。
在西方一些国家,博物馆是作为公共空间进行管理的,通过基金会,其属性也必须属于公众。而中国的博物馆馆主,通常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收藏,所有权问题也变得很暧昧。在藏品上投入了巨大的身家之后,因为与市场的紧密挂钩,一切都变得更加诡谲,博物馆或者成为洗钱的工具,或者成为文物倒卖的黑库,或者变成一张商人的护身符。
也或者,像朱成这样深陷其中。
奇怪的悖论产生:私人收藏家们的收藏热情,加剧了盗墓现象的产生和文物的破坏;但他们完全出乎个人的热情和劳动,又为这个社会保留了巨大的公共财富。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父子两人都忍不住发起了牢骚。儿子朱明窝着心头的火,他说,其实只要动员一些西方馆藏家、艺术家介入这件事情,很容易被迅速的重视起来。但是——
“大家都是中国人,我真不想丢脸。丢脸——也不是丢我的脸。”
“看嘛,谁都不要逼我。”他小声嘟囔着。
朱成的叹息,则要古典多了。他有时说:“其实可以把这些土里的东西埋回去,这个时代不配。”
有时又呵呵自嘲:“啥子美学?这就是贫穷美学!”
“狗屁的贫穷美学!”朱明怒吼——这句话自然不是对老朱喊的。空荡荡的房间里,这个青年艺术家原本温润的声线,在跌宕中变形。
—— (五) ——
体育馆改造发现蜀王宫遗址的消息,在三月中引爆了成都人的朋友圈。成都人爱调侃:以前在体育馆里看演唱会——几万人在坟头蹦迪啊。
月底,我和考古系统的马麟,张行三人,再一次拜访了朱成石刻艺术博物馆。还没走到,就听到轰隆隆的声音。有人说是挖掘机在挖河道。具体为什么,就不知道了。
马麟想了想:“是不是府河的景观改造启动了?” 今天老朱没在,老刘在院子里坐着,说朱大爷去市政府开会去了,不晓得好久回来。我们转了一圈,准备到对岸的露天饭馆去喝茶。刚到吊桥边,看到桥居然断了,几个工人正在用板子把路封起来。
“咋回事?”
“挖挖机把桥挖断了!”旁边看热闹的村民乐呵呵地说。
▲ 清理河道的挖掘机 【图片】田坤
成都北改,已经进行到了第七个年头,开始进入最后的冲刺。紧挨着凤凰山片区的上府河生态景观改造,是成都北改的最后部分。这一阶段之后,像青杠林村这样的城中村,将在成都荡然无从。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涌入成都,期待着成都的慢生活,视它为新故乡。这座城市发展速度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本地人眼里的成都,正在逐步加热,生活速度追着房价一起上浮。今年三月,随着一道“限购令”的出炉,有人放声大哭,更多人的话题,从晒太阳打麻将,换成了房子。
▲ 博物馆外的茶摊 【图片】田坤
我们绕了一大圈,才绕到对面的茶园子里。因为吊桥断了,来的客人很少,老板娘哭丧着脸。
“这里要拆迁了,你们准备去哪?”我问。
“不晓得嘛!”老板娘满脸愁容。
“你们喃?”
旁边的村民哄笑:“住安置房噻!”
在院坝头坐着,晒太阳,啜一口茶,昏昏欲睡。马麟张行两个,聊着天府新区的房价。老马说单位系统内在建一个小区,就是离上班地方太远,犹豫要不要买。老张却忽然拍一下大腿,吓我们一跳:“唉,你记不记得刚才看到的一个井栏子!?”
老张说记得,怎么啦?
“蜀王宫遗址,里面有个斗斗井噻!只有井,上面啥子都没得——就缺朱大爷收藏的那么一个井栏子!”
老马兴高采烈,老张说对哦对哦,也高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