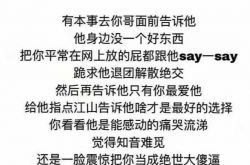“你去过果园吗?”她问我。
我摇摇头。
“你可以去一趟看看。去看看果子是怎么生长的。看看柿子怎么变红,看看浆果怎么膨胀,看看核桃怎么从吹弹可破变得坚不可摧。”她说,“去看看生命的能量。你知道生命的能量有多迷人吗?”
她用脆生生、活泼泼的声音说着这样的话,我一时间忘记了她手里还拿着一张重度抑郁诊断书。
“我是个坏机器。”“我只有被修好才有可能被爱。”
她第一次做心理咨询是在高中的时候。我问她是从哪知道心理咨询这回事,她说是从家长会分发的家长手册上看见的。
当时她上的是一个全封闭高中,管理很严格。妈妈在家长会上拿到了家长手册,没有仔细看,但是被她拿走认真看了。
“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时,要积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手册上这么写着。
“我突然之间就明白了。”她说,“啊,原来还可以这样啊。
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是心里面哪里出问题了;
心情不好的时候,还有心理辅导这种方法可以用。
心情不好原来也是可以修好的,我还不至于那么无可救药。”
“天啊,”我插嘴,“你好棒。我只会想着,‘对,我就是无可救药’,然后自大地认为谁也救不了我。”
她摇摇头。“因为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被修好’,是获得爱的唯一方法。”
进入高中以后,因为成绩大不如前,她每一天都要面对很严重的焦虑。高中的实验班,落下来一次就糟了;对她来说学习这件事像被施了最恶毒的咒语,一旦靠近它就会被焦虑的纺针刺破心脏。
“妈妈把一切都照料好了,我只要全心全意学习就可以。”她说。
“但我太焦虑了,我唯一无法做的事情就是学习。
一切都很好,只有我不好。 ”
她觉得自己承受不了;学习焦虑本身、逃避学习带来的愧疚感,以及成绩下滑之后的无用感,每一件每一件把她搅进漩涡中央。
但她明明已经要承受不了了,妈妈还对此一无所知。坚强点,妈妈说,我给你找了家教,勤奋点。成熟点。看开点。加油。不要再让我失望了。
“妈妈能把一切都照料好,除了我的情绪。” 她说,“妈妈为了我能好好学习,为我忙里忙外焦头烂额。我的理智总是告诉我,一切都很好,妈妈很爱我。可是她的爱,在那里,我看得见,但是得不到。”
父母们总是一无所知。父母们全心全意地爱着孩子,但总是不知道自己忽略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传达了什么。
妈妈的爱,在她眼里都是带着附加条件的。妈妈的爱,在那里,但不属于她,它属于那个坚强、上进、优秀、从来不让人失望的她。
既然这样,那就去找人来修理自己好了。偷偷地,不要让母亲发现地,找一个人来修好自己。
“我希望一次心理咨询就能解决我的问题,”她说,“像修一个机器一样一次性把我修好,接下来我就能 正常地运转 了”
说“正常地运转”,她是指考试和学习。
那个时候她真心实意地觉得自己是一个坏掉的机器,只有被修好才有资格获得爱。
“我明白了,没有人会愿意接受我。”
“但我竟也对此毫无感觉。”
当时她对心理咨询的所有理解都来自她在搜索引擎上看见的内容。这些内容把心理咨询写得神乎其神,她不知道咨询师打算怎么一次就“修好”她,但她像抓着救命稻草一样这么想着。
为了获得那根救命稻草,她瞒着妈妈攒了好久的生活费,凑够了第一次的咨询费用。
咨询师当然也是搜索引擎上推荐的啦。
她不知道自己要见到的咨询师是男是女,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擅长处理什么样的问题。但她相信这是修好她的唯一方法,所以她义无反顾地就去了。
“第一次咨询感觉怎么样?”我问她。
“我感觉,”她笑了,“这都是什么鬼玩意呀。”
那不是她的救命稻草。
那是稻草,没错的,但那是压垮她这只伤痕累累的小动物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位咨询师坐在办公桌后面,穿着白大褂,口袋里搁着一把钢笔。他抱着手臂,嘴里说着直接从心理咨询教科书上摘抄下来的话,动作和表情却明明白白地拒她于千里之外。
她感觉被这位咨询师拒绝了。
“你失望吗?”我问她。
“不失望。”她说,“我没救了。这是我那个时候唯一的感觉。除了这一点,我什么也感受不到。”
“心理咨询师都修不好我。心理咨询师都不愿意接纳我。心理咨询师都想离我远远的。没有人打算爱我了,没有人打算接纳我。”她说,“那个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没救了,我这一生再也不会有感觉了,我完蛋了。”
从那次之后她也开始拒自己千里之外。她像忽视她情绪的母亲一样,开始忽视自己的情绪;她像不愿意接纳她的心理咨询师一样,开始拒绝接纳自己。
“你当时有意识到你可能得了抑郁症吗?”我问她。
“没有。”她说。“我根本不会往那方面想。我觉得抑郁症是一个好的人生了病,这个人,无论他怎么寻死觅活,他只是生了病。但我不是。我本质上就是糟糕的,我不是在生病。我是糟糕的,所以我要把我的糟糕藏起来。”
她给自己罩上了玻璃罩子,这个玻璃罩子隔开了她和周围的人。她变得“开朗”,变得“乐观”,变得“积极向上”。周围每一个人都相信了,朋友们相信了,老师们相信了。
妈妈也相信了。
她给自己罩上了玻璃罩子,这个玻璃罩子也隔开了她和自己。她无视自己的情绪,她不想再感受自己的情绪,她把问题藏起来,丢在了一边。
“可是课业呢?”我问她,“还是很焦虑的话怎么办?”
她盯着桌面的花纹沉默了一会。“说出来你不要觉得奇怪,我那时其实真心地觉得,我这么年轻,把生命花在课业上真的太浪费了。我明明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但我也不能做了。我压抑着自己在学习。我在学习了,这算被修好了吗?”
我犹豫一会,摇摇头。
“我开始觉得我要对妈妈的情绪负责。” 她说,“我已经不指望她给我什么支持鼓励,不指望她照顾我什么情绪。只要她高兴了,我就安全了。你知道松子吗?被嫌弃的松子?她在父亲不高兴的时候就会冲他做鬼脸。我和她一样。我会冲妈妈吐舌头,略略略。”
她伸出舌头示范“略略略”,笑了一会,又安静下来。
“每一件事我都先想到最坏的结果。” 她说,“我无论做什么,都等着最坏的结果,都等着妈妈失望,等着妈妈训斥我,等着她说她不再爱我。事情已经不会更糟了,她骂完我,她就会高兴了。她高兴了,我就安全了。”
“爱都用不着,用不着爱我,我只要安全。”她说,“我就这么想着,活了下来。”
“我受得了他冲我发脾气,但受不了他不理我。”
“我甚至希望他冲我发脾气。”
刚上大学的时候她放松了很多。
她恋爱了。
但她的第一场恋爱,糟糕得就像她想象中的,她和母亲的关系。她想象她每做一件事都会被母亲训斥,她想象她母亲总在狂风暴雨一般冲她咆哮,而这种狂风暴雨令她感觉安全。
于是她总是暗示这位男孩粗暴地对待她,暗示他可以冲自己咆哮,暗示他遇到不顺心的时候都可以冲自己发火。而这位男孩,不但全然接受这些暗示,还严谨地一条一条全部照做。
她对母亲、对亲密关系的所有“期待”,全部成真了。“那种感觉就好像他拿着刀子要刺向我,我嫌他力气不够大,就帮着他握住刀柄,刺进我的胸膛。”
她的第二段恋爱更加糟糕。第二位男友,“他虐待我的方式不是我想要的,”她说,“他忽视我。这是我受不了的。你可以指责我,可以骂我,甚至可以不爱我,但不可以忽视我。”
“你是想要爱的。”我说,“爱如果不能以关怀的形式出现,那它也要以虐待的形式出现。所以你才受不了忽视。”
“对。”她说,“可是我花了好久才弄明白这一点。”
她为了理解自己的行为,也为了理解她周围的人们——妈妈和男朋友——都在想些什么,她开始重新对心理咨询和心理学感兴趣。
大学毕业以后,她重新开始寻找咨询师。
“你知道淘宝上也出售心理咨询服务吗?”她问我。
我近乎惊恐地摇摇头。
“不要买,”她说,“太可怕了。”
她在淘宝上购买了所谓“心理咨询”服务。就像购买普通商品一样,她选择价位以后下单,就立刻有人打电话来为她“提供服务”。
他们在一点也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隔着听筒里沙沙作响的电流声,要进行“心理咨询”。
“那种体验太可怕了,”她说,“他们不明白我,对我说一些无关痛痒甚至评价指责的话,我几乎都重新体验了一把高中第一次做咨询之后的感觉。觉得自己糟糕又无能。”
“那你有投诉吗?”我问她,“或者太过失望就放弃心理咨询?”
“我不会想着要投诉,”她说,“我只想着,这个咨询师不行,我就换一个。反正他们的服务都很便宜,”说着耸耸肩,“我总能找到那个真正能帮助我的人。”
“你真的,”我说,“太厉害了。我这么说你会不高兴吗?我觉得你的生命力好顽强。”
“我只是太需要帮助了。”她说,“我对心理学知识了解得越多,我就越需要帮助。你知道,很多心理学畅销书都会说这些道理。
在放弃电商平台以后,转向了医药类手机软件。“上面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她说,“购买服务了的话,就会有人来同你聊天。语音聊天或者文字聊天都有。”
她购买了一个包双周的服务,在这两周内,她随时都可以和一位“咨询师”聊天。
“有用吗?”我小心翼翼地问她。
“有用。”她说,“但是你就想象,我是一个躺在病床上的将死之人,这个人剖开我的胸膛,用手捏着我的心脏,靠挤压让它跳动,那种类型的有用。”
这位陪她聊天的人,基本上是用了最严厉的词语,斥责她懒惰、脆弱、没有用,希望用这些话“打醒”她,甚至,“激励”她。
“我的心脏在跳动了,”她说,“但我不觉得我活着。”
“你不接受我也没关系,我会继续找其他咨询师。”
“但请你不要伤害我。”
这之后她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孤独的旅客,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山崖失足跌落。没人发现她已经在山崖底下不知死活地躺了许久,久得连她自己都快要忘记要醒来。
但是有一天,她醒来了。
她摔得太疼太疼,她终于意识到要认真地为自己找一名真正的心理咨询师。
“你又要拯救自己了。”我说,“你太厉害了。”
“我躺在悬崖底下,疼得都没有感觉了,但我不能一直这么躺着。没有人知道我躺在这里,我要活下去,只能指望自己。”她说。“所以我挪呀挪,挪呀挪,说不定就能碰见给我搭把手的人呢。”
这是她生命力的触底反弹。
她在某个平台上寻找咨询师的时候,是她为自己体重感到最焦虑的一段时间(“生活里有什么不值得焦虑的,对吧?”)。她下意识避开了那些在她的标准里显得“美丽”的咨询师,最后选择的是一位看起来很圆润很亲切的咨询师。
因为她坚持认为,“美丽的人是不可能接纳我的。我太丑陋,太不堪。”
她不知道该在要求栏写什么,就把自己之前的经历一五一十全写下来了。在经历的最后,她写,“如果您觉得我不合适,您不知道怎么处理我,没有关系,我会继续找其他咨询师的。”
“您不能接受我,没有关系,但是请不要伤害我。”
她写下这样的话,之后就像她处理每件事的方式一样,等待被拒绝,等待最坏的结果。“我还以为咨询师会立刻把我的订单取消,”她笑着说。
但那位咨询师没有这么做。咨询师告诉她,“我对你很有兴趣,我很愿意了解你,”甚至还说,“我很期待见到你。”
“之后就见面了吗?”我问她。
“见面了。”她说,“但我到她门口的时候,犹豫了很久不敢推门。”
不敢推门是因为,这一次再被拒绝的话,她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醒过来了。
“这一次咨询你感觉怎么样?”我问她。
“具体和她说了什么,我自己都不记得了。”她说,“但我记得,我一直在说,她一直在听。每次我觉得她可能要开始觉得我烦,或者打断我的时候,她都没有。”
“这一次咨询的最后,”她说,“咨询师说,一开始她看不见我的问题。我看起来这么健谈,这么外向,这么乐观,我罩着玻璃罩子呢,她当然看不见我的问题。”叹了口气,“但她听我说完所有的话之后,她感觉整个屋子里都充满了之不去的悲伤。”
“我的眼泪一下子全下来了。”她说,“我在她面前整整哭了半个小时。”
她终于被看见了。 终于有人知道她不是作,不是自作孽。终于有人移开了她的玻璃罩子,切切实实地触摸到了她的悲伤。
“我终于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她说 ,“我要被爱。我要被看见。我要我的感觉被承认,我要活着。”
她从这位咨询师那里,第一次知道自己拥有的那些情绪不是错的,知道自己觉得难过也不值得怪罪;她也第一次知道,自己如果有错,那就错在了对母亲的期待上。
“我以前从来不会同母亲倾诉情绪,因为我的情绪是错的,是羞耻的,是需要藏起来的,是不能同母亲分享的,这是我一直自以为安全的生活方式。”她说,“可是这是错误的。我要先承认自己的情绪,才能希望母亲承认我的情绪。”
她对母亲的那些期待,那些母亲总会训斥她、总会对她发脾气、总会对她失望,等等这样的期待,是错误的。她开始相信母亲是无条件爱着她的,只是母亲也不知道怎样表达。
所以她需要教母亲来爱她。
“大概是已经做了几次咨询的时候,”她说,“我实习的公司,因为我几次缺勤,基本上扣光了我那个月所有的实习工资。我太难过了,忍也忍不住,所以我想到了妈妈。”
“我在电话里和她倾诉完,心里还是习惯性地觉得她一定会说我做错了,会说公司做得对。”
她说到这里叹了口气,“我心里也隐约觉得公司做得对。这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但是这些话要是从妈妈嘴里说出来,会很可怕的。但我已经从咨询师那里知道了她可能不会这么说,所以我壮着胆子向她提了一个要求。”
“你可以安慰我吗?”当时她问母亲,“我真的很难过。”
这是以前的她绝对不可能说出口的要求,是她怎么也不会向母亲伸手索要的东西。
“妈妈说什么了?”我问她。
“妈妈说,”她回答,“这个公司真糟糕,你受苦了。”
她说完这句话,像在回味刚刚坐的云霄飞车一样,对着空气陷入沉思。
“感觉怎么样?”我问她,“听妈妈说出那样的话?”
她眨眨眼,回过神,看着我的眼睛说,“爽翻了。”
“妈妈说,宝宝,我终于知道你有多难过了。”
“一瞬间我就明白,我期待的东西终于来了。”
“你真好。”我说,“你从来没有放弃自己。”
“我想过放弃的。”她说,“有一次我和妈妈在街上因为心理咨询的事吵架了,我几近崩溃,跑到马路中央,指望有车能撞死自己。那是我最后一次想要自杀。”
告诉妈妈她在接受心理咨询,是最重要的一关。
她第一次和妈妈说起这件事,是一个异常平静的夜晚。她和妈妈无所事事地围着电视,她看着妈妈,心里突然涌起强烈的、被接受的渴望。于是她没有多想地同妈妈坦白了自己正在接受心理咨询。
“如果没什么事就别做了。” 这是妈妈的回答。
她一下又感觉自己挂在了悬崖边上。
之后她们又为此争吵过好几次。妈妈不了解心理咨询,也不了解心理疾病,她宁可相信女儿只是闹脾气,宁可相信她只是个“不高兴的小孩”。她给妈妈看了有关抑郁症的小册子,妈妈看了一眼,说,“你没有得病”。
——让一无所知爱着她的妈妈接受她有问题,是最重要的一关。
“我知道她为什么这么说。”她说,“哪位母亲都不会希望自己的小孩生了病。哪位母亲都不希望自己的小孩在一个那么危险的境地,危险到需要去做心理咨询。”
但她需要母亲承认。这一刻她需要母亲的承认,这一刻母亲的承认重逾一切。所以当母亲又一次拒绝承认的时候,她绝望地冲到马路中央,指望有哪一辆往来的车辆,能大发仁慈地撞死她。
像她之前提及的,这是她最后一次想要自杀。
“但你最后没有自杀。”我说,“这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是我自己救了自己。”她说。“我站在马路中央,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思考不了。但迎面驶来的轿车终于要撞上我的时候,我的身体自己动了。我自己,不经我的同意,救了我。就像以前每一次一样,我,救了我自己。”
既然这样,她就要继续拯救自己。她决定带着妈妈去医院做心理诊断。在去医院的出租车上,妈妈握着她的手,祈祷一般地重复,“我们没有抑郁症,我们只是有抑郁症状,好吗?”
“记得我之前说我不认为自己生病了吗?”她说,“那一刻我不这么想了。我从来没有这么渴望被确诊抑郁症。只要有那一纸诊断书,我所有痛苦都有了证明。证明我不是作,我不是心情不好,我不是坏小孩。证明我,是一个好的人,只是得了病。”
证明她虽然比别人活得更辛苦,但她还是很努力地活着;证明她的身体里储藏着的那么多沉甸甸的生命力,她一点儿也没有辜负。
她在医院拿到了她重度抑郁的诊断书。
其实在此之前妈妈心里是有数的,她知道,妈妈也知道她知道。
妈妈只是太害怕了。在妈妈对抑郁症有限的了解里,抑郁症是个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可怕怪物。在媒体报道和各种影视作品里,抑郁症总是和自杀一同出现。所以在没有确认它真的在眼前之前,她只希望自己的女儿能离这个怪物远远的。
但是诊断书拿到手里的瞬间,侥幸的心墙也轰然倒塌。
“宝宝,”妈妈用力地拥抱了她,“你太辛苦了。”
你太辛苦了。你太难过了。我让你失去保护地一个人承受这么久。我现在都知道了,你究竟有多辛苦。
“那一瞬间我就明白,”她说,“我期待的东西终于来了。我的痛苦终于被她了解,我的情绪终于被她看见,我为活着所做的努力终于被她承认。我在她的怀里,这一回我是真的安全了。”
我说不出话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后来我参加了好多线上的抑郁症患者自助小组,”她说,“各种平台的都有。贴吧的,豆瓣的,还有qq群。不同平台的抑郁症们,连气质都不大一样。你知道在这些小组里也是有‘辈分’的吗?病史越长,地位越高。”
在这些小组里,大家分享的心情和想法,通常是会得到抱持和理解的。她经常在小组里开导别人,告诉他们“不是你的错”,建议他们去寻求帮助和治疗。
“你的生命力旺盛得都溢出来感染别人了。”我说。
“其实很多患了抑郁症的人,他们并不是没有生命力。”她说,“自暴自弃,甚至自杀,这是他们对自己生命的另一种掌控方式。如果不能使它们生长,那就使它们毁灭。”
但拥有生命力本身,已经足够了不起。有时候我们只是需要一些帮助,以及一些皎如日星的爱。
“你有去过果园吗?”她问我。 我摇摇头。
“你可以去一趟看看。去看看果子是怎么生长的。看看柿子怎么变红,看看浆果怎么膨胀,看看核桃怎么从吹弹可破变得坚不可摧。”她说,“去看看生命的能量。你知道生命的能量有多迷人吗?”
我知道生命的能量有多迷人吗?
“我知道的,”我看着她,笑了笑。“我正看着它,并为之着迷呢。”
后记
在我写作这篇访谈之前,我惴惴不安地以为,讲述一位抑郁症患者的故事可能会给我自己带来一些创伤。
但到最后,我竟然在她那里得到了治愈。还有什么会比努力向爱生长的生命更动人的呢?
现在的她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抑郁症,但她还在努力。
标签组:[心理学] [心理咨询] [焦虑抑郁症] [咨询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