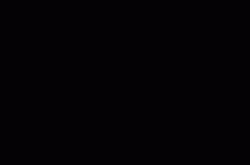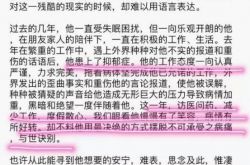「其实,我的内心是极不安分的一个人,谁也别想把我固封住,永远不会的,绝对不允许。」他说。
「这么多年,没有一瞬间想过真的算了?濒临想要泄一口气的时刻?」我问。
「没有。」他立刻回答。顿了下,他紧接着说了第二个,「没有。」像是确认某件事情,他持续地摇头,没有没有没有。
1
演员刘奕君曾经想让自己长成西安城外麦穗的模样、高粱的模样,因为他太漂亮了。但在51岁这一年,他为《人物》拍摄封面这一天,离开镜头,他的脸上更多是一种普通。
他曾经在上海虹桥火站看到一对母女讨饭,便给孩子点了炸鸡。孩子说,要拿回去给爸爸吃,他又给她们一人点了一大碗牛肉面,就在这儿吃吧,他说,让孩子把炸鸡带回家。也许她们是骗子,只是想要一点钱,刘奕君不会给钱,但善良又不允许他旁观。
「那时候我已经还可以了,大众的认知度都有了,但是她们俩不认识我」,刘奕君说。他经常去一些小店吃饭,没人认出来。尤其去外地拍戏时,他一个人去吃小吃,一笼包子、一碗面或者一碗粉,旁边是喧闹的务工的人,他感到安全。他知道自己在荧幕上的样子跟本人差别很大,他愿意自己在生活中普通。
很长时间,刘奕君都是人群里惹眼的漂亮小孩,十几岁长成,五官精致,唇红齿白。父亲的朋友夸他形象不错,可以进京考个表演系。17岁,他成为北京电影学院87级表演班最年轻的学生。北影教授李苒苒今年87岁,是刘奕君大学时期的老师,她回忆起34年前第一次见到刘奕君的场景,笑出声来,「哎呀,那是一张小圆脸。有点小孩子气的老实孩子。」当年,北影老师们都觉得,从形象上看,刘奕君的戏路不会太宽阔,「以为他将来也就只能演个年轻人。」李苒苒说。

一个好帅的小生,这是李雪对刘奕君的第一印象。2000年,他们相识于古装剧《人鬼情缘》剧组,那年刘奕君30岁,扮演男一号宁采臣,李雪26岁,刚跟着导演孔笙进剧组,是那部戏的摄像师。李雪说,当时的刘奕君身上有一种古典的、老派的、近乎戏曲演员的气质,大家看到宁采臣的那张脸,「都觉得他是一个天生的好孩子。」

这张好孩子脸与它散发的乖巧气质,一度是刘奕君最大的烦恼。
他毕业的1991年,是第五代导演蓬勃辉煌的时期。《黄土地》《红高粱》《猎场札撒》散发着粗砺的、犷悍的、原生态的审美气息,但刘奕君和这些词一点关系都没有。同学王全安在西安当副导演,想帮他找个活儿,见了导演,西安娃刘奕君特地说了两句陕西方言,被一句话打发走:太漂亮了,不像咱陕西人。
「乖」和「好」牢牢框着他,不能伸胳膊伸腿。同学里有会应酬的,有在外面工作过有些社会经验的,他什么都没有。有段时间走在街上,路过服装店,他会跑过去,「啪啪」,用帽子打两下模特,然后开溜,这是他的办法——让乖孩子看起来坏一点,痞一点。
1991年,刘奕君毕业,按照规定,除非找到接收单位,所有学生都要分配回原籍,刘奕君被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他发现,在北京学了四年表演,他即将回到高中时那种一张白纸、谁也不认识的状态。怎么办?有天午睡,他突然醒来,发现脸上全是泪,那是他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生生被自己哭醒了。梦里的故事他不记得了,但那种对未知的恐惧、慌张,时隔30年还清晰可感。

2
刘奕君至今可以完整复述出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台词,他模仿当年的翻译腔,「不要过早地把油箱打着」,他的语速越来越快,到最后手舞足蹈地表演起来。
在电影学院,李苒苒也发现刘奕君是个很容易「相信」的人,相信人物,相信规定情境,不是每个学生都能这样。他认为,这是他对表演最真,最纯粹的欲望——就是想要演,想演好戏,好人物。
但西影厂的日子苦闷难耐,21岁的刘奕君被分配到西影厂人劳处,主要工作是统计员工薪酬。每日骑着单上厂里,喝着茶抄着工资表,一天就过去了。实在没事干,跑到同学王全安的宿舍打魂斗罗,连打好几宿。偶尔他会惊觉,从中抽离,租一些经典的录影带看,「看电影的那一瞬间,你会忘了生活的残酷。」电影提醒他,别忘了自己是一个表演者。
电影结束,他又回到了庸常的抄表生活。
一直不能接受,一直伺机而动,那时候他只要瞄到机会,立刻要扑上去。2018年,他接受《鲁豫有约》采访,说过一个形容,「猫在打盹的时候,事实上它睁着一只眼睛观察哪儿有响动,哪儿有动静,它会立马全神贯注地去出击。」
1992年,有部戏找他当男主角,他高兴坏了,不管厂里开职代会,连领导面儿都没见,留下一张请假条就走了。如痴如醉拍了一个多月回来,直接领了留厂察看的处分。第二年,他被宁波电视台台长看中,离职去南方拍戏。但他仍然不是演员,而是一个导演。
他写剧本,选演员,统筹执行,做的大多都是幕后工作。他给谢衍的电影《女儿红》当执行导演,和归亚蕾、周迅、顾美华合作,他无限接近现场,接近演员这个职业。导演他当得不错,他编导的8集电视短剧《漫记人间》获得了全国星光杯二等奖。
这一切都没有吸引力。回忆在宁波生活的两三年,他说那是一段最容易放弃的岁月。他有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又重新拥有了稳定的环境,以及,他体验到了作为导演掌控全局的权力感。但这都不是刘奕君想要的,他想要的还是那件事情:表演。
毕业七八年,同学腾腾腾起来了,隔三差五出现在荧幕上。只有刘奕君消失了,父母、朋友、亲戚都知道他学表演,但毕业后再也看不见他。
他开始真正反省自己此前的「乖」,「你就不会思考,你活在别人的评价里,但是评价的人慢慢不稀罕评价你了,或者评价的人都不在你身边,那些东西不重要,或者说你为了生存,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已经不在意别人的评论了。我要生活下去,我要生存下去,我要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个时候你才会想我应该怎么办,逼着你把丢掉的思考能力捡回来。」
他不停地看电影,念台词,他通过这样的方式假装体会表演的快感,「(做这些是)为了心里的火苗,用双手护着它,别灭了。」
有经历过生活难以为继的时候吗?
有啊,有啊,他答,没有犹豫。站在功与名的当下,他不愿再谈起那段困窘日子的生活细节,但那种求而不得的状态一直留在生命中。「我说我是不是一匹能跑的、善跑的马,你得让我跑,跑了之后,我真的不行,我扭头就走;可连跑的机会都没有,那不行,那不行,我必须要找到这样的机会,但是我一次机会都没有,不甘心,不甘心。」
那段时间在他脸上留下痕迹,最近在拍的戏里有个女演员,当年他日子不顺的时候就认识,他是副导演,她是演员,他站在摄影机后头看着她演戏。她保留着一张当时他们在一块玩的照片,这次拍戏又拿给他看,胶原蛋白充足,但纠结和拧巴都在脸上。
1997年,中国电影电视市场开始发生变化,《过把瘾》之后,出现了诸如《永不瞑目》《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等等青春爱情片,刘奕君发现,自己那张精致的脸不再是阻碍。

运气好像突然眷顾了他,但李苒苒说,此前的窘迫不是刘奕君一个人的困境,是一个班、一个年级甚至是一批演员的困境。1994年之前,中国几乎没有超过20集的电视剧,被看见的机会凤毛麟角。有人放弃,有人转行,有人颓废,「87、88、89那一批,他们都稍微地,停了那么一段时间。」
这个「稍微」,是十年。像一艘船终究启动,刘奕君四处张望,发现船上坐着的都是他的同学,有人撑篙,有人划桨,从北影的河道出发,驶入中国影视的海。
3
最开始,谁也没想过刘奕君能扮演一个坏人。而且,此后他会因为反派的人物形象在中年走红。
2007年,孔笙筹拍《绝密押运》时提议,让刘奕君来演个大坏蛋吧。包括李雪在内的其他团队成员都很惊讶,「孔导怎么会让刘奕君演坏蛋?还是个坏蛋的头头!他明显是一张好人脸。」看了刘奕君的戏份后,李雪觉得,孔笙导演挑选演员的眼光还是十分独到,而且,他明显感觉到刘奕君在那部戏得到了一种「释放」。那也是刘奕君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扮演一个反派。

多年后,还有人在网络上谈论当年刘奕君扮演的项洛阳,一个高智商的犯罪分子,因为出身穷苦,想尽办法让自己变得富有。故事接近尾声,项洛阳有这样一段戏,他噙着泪说,人可以过穷日子,但有了钱之后就不能再受穷了。有网友评论:感觉这个演员也经历过类似的窘困。
2009年,刘奕君出演《开创盛世》中的隋唐佞臣封德彝,他说那是一个可以跌落尘埃的人,没有主角的光环和道德约束,尽情溜须拍马,撒泼打滚,「没有主角光环或者道德的约束,一下子解锁了我很多功能,似乎能够把一些阅历用到角色里了」,他说,「没想到我演得那样好。」

对恶的呈现在《伪装者》和《琅琊榜》时达到了巅峰。老艺术家智一桐在电视上看见王天风,特意翻出电话号打给刘奕君,「看了你的戏,我太吃惊了,导演是谁啊,用什么手段把你逼成了一个疯子?」此前,他们失联了20年。
刘奕君很清楚,拍摄《伪装者》的时候,导演李雪没有逼他,让王天风呈现出疯狂而极致状态的是过去20年的经历。「那疯狂的状态随时就有。我当时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我知道了,就是那段不如意的岁月在你心里留下的种子,你想发泄,你想反抗,但是没有地方去反抗。然后,碰到这个角色了,一下子就掏出来了。」

他做过一个比喻:每次扮演恶角,相当于把你的灵魂出卖给那个恶人。他要从身体里掏出这种恶,还要找到这种恶,最终,为了角色,他还需要保护这种恶。「要把刘奕君本人和善的部分全挤到一个角落,咔——锁住,最近别出来啊。」
他演过最恶的角色是《远大前程》的张万霖,一个没有任何温情和耐心、杀人不眨眼的黑帮老大。有天妻子带着女儿去探班,他让助理去接,等了20分钟,他不耐烦了,顶着白毛,穿着长袍,挂着大金链子,冲到门口,看见妻女还被锁在门外,助理正在特别礼貌地交涉,他嚷嚷起来,「怎么搞的!到现在都没有进来!」妻子看着他,「刘奕君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凶神恶煞的?」

那段时间,他成天做噩梦,梦里都在杀人,演到后来都抑郁了,刘奕君告诉演员富大龙,「大龙我想哭,我以后再也不演这样的角色了」,富大龙安慰他,说特别能理解他。
「我演任何角色心里必须得有,心里没有,我演不出来,他那种攻击性,那种恶,就是你心里必须装着恶,从你心的箱子底翻出来,还得保护住这种恶,对我来说多么残酷啊。」
刘奕君的个人史,是从善到恶的历史,曾经一个特别乖的孩子想要变坏,想要让自己内心那点坏伸手伸脚,当他终于能在反派的表演中无限伸展时,又觉得这种伸展太过强烈。一个人终将发现自己的尺度,他说,不喜欢被人问「你又演了一个坏人啦?」人是最复杂的,黑白灰都有,「我只是演了一个复杂的人。」他想这样回答。
演员华子与刘奕君相识20多年,他们不是通过合作认识,也不是通过演员聚会。而是华子无意在电视上看到了他,觉得这个演员有意思——明明是一个配角,可能从他的表演中感觉这个人物内心藏了很多事,「(角色)没那么复杂,都让他给演复杂了。」

《伪装者》里,刘奕君扮演的教官找到面粉厂,从于曼丽手中拿过棒棒糖。李雪的要求是,拿过棒棒糖游走过来,走回到椅子,「如果不介意的话,你拿棒棒糖舔一下,显得这人瘆得慌」,刘奕君果然把棒棒糖放进嘴里,「咔嚓」,咬碎了。
「他眼睛里的(恶)永远给人一种很复杂的表达。」谈到此处,电话那头的李雪突然停顿了几秒,「哎呀,真的是,真是这种演员不好找了。」

这是刘奕君最好的时候,他还会越来越好,李雪说,「当他眼睛里多了很多东西,脸上沟壑也多起来,就不一样了。30岁和37岁的他完全是两个人。他能给人传递出来的信息不是单一的,是更综合、更丰富的信息。」
他终于像心中所想,长成了麦穗,长成了高粱。

4
一个14岁的男孩想要当演员,可是当演员的父亲不同意。
劝说父亲刘奕君同意自己报考电影学院,刘怡潼花了两年时间。父亲很坚决,害怕儿子太累,刘怡潼不理解,认为累就是早出晚归,冬日拍夏天的戏,身体吃不消。后来才明白,父亲说的累,是心理上的折磨。

刘奕君常拿自己举例子:我蛰伏到四十多岁才有了名气,你才20岁出头,万一命好,能有起色;命不好,能熬得下去吗?如果看着同学纷纷蹿起来,你的事业毫无波澜,你还能坚持这条道吗?
刘怡潼说,父亲从来没有当面表扬过自己。父子俩谈话,刘奕君很少点头,也很少肯定。他不觉得荧幕里的父亲,王天风、谢侯爷、张万霖有多么狠,因为在家里刘奕君一瞪眼,刘怡潼都会害怕,「完了完了,又要蓄力了,又要发功了。」他们曾在一部古装剧扮演父子,当父亲穿上帝服,浓眉长须,刘怡潼觉得又看到不怒而威的爸爸,对戏时紧张得卡了好几遍台词。
后来,他听朋友说,父亲在别人面前夸他,还拿照片给别人看,我儿子这么大了,一看以后就是演男一号的脸。这些话,刘怡潼从未听过。
他只是知道,小时候自己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有时,一觉醒来,看到父亲坐在床边,看着他。前一阵子,刘奕君拍完戏回北京,父子朝夕相处半个多月,刘怡潼使了点小心思,劝父亲晚上跟自己喝点。「不会喝太晚」,结果喝到凌晨两点多,说了很多细细碎碎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已经长到可以和父亲促膝长谈、推杯换盏的年纪了。第二天早上,父亲又冷了脸。
在刘奕君看来,演艺行业是一个人声鼎沸的餐厅。所有人 「从门口一点点进,进到餐厅里,一点点从边缘的桌子,慢慢慢慢地才坐到主桌上吃饭。」从门口到主桌,刘奕君比谁都清楚这个过程有多么辗转曲折。
李雪记得,筹备《北平无战事》时刘奕君主动请缨演一个反派角色,导演团队选来选去,还是给他一个正面角色。李雪说,刘奕君是一个不吝于表达的演员,他会主动地表达这样的「要」,要一个剧本,要一个角色。这不止是维持生计的问题,「他总是涌动着想要创作,想要参与,觉得自己有各种可能。」

每次筹备新戏,孔笙、李雪、侯鸿亮都会想到刘奕君,但他并不是每次都能得到想要的角色,甚至连个角色都没有。李雪说,他从来没有给过他们压力,「他身上有一种70年代、老辈人的态度。他不会天天说『导演,你给我个角色』,他做不出来这种事情。但他的表达能让你感觉到,我这个人在,我有心气儿还想演好戏。」李雪说,刘奕君是一个很懂得克制的人。他会克制那种不甘心,克制那种冲动和欲望,包裹住它们,再与人交往,珍贵的是,他把所有的不甘心都放在了演戏这件事上。
他不愿意与生活和解,即使和解可能是更理性、更正确的选择。2005年中秋,他和一个朋友在巴州办事处吃完羊肉,从西直门走到三环,走到北展,走到天安门,又走回北展,聊人生,聊月色。那会儿天安门旁边还有人卖哈密瓜,一牙一牙切好了摆着。他很少当街买水果,觉得有苍蝇,但朋友劝他,来来,吃吃,乘着兴致,他也吃了一块。
哈密瓜的味道现在还记得,皎洁的月色现在还记得。那时他仍然不能完全演到自己想演的角色,但他记得生活里那些琐碎的快乐。他更愿意记得快乐。
那时他已经35岁。人到中年之后要很小心,可能一不留神选择了一个解压方式,吃,喝,泡吧,这些方式没有错,但对一个演员来说,它将阻挡你向上。刘奕君一直谨慎地活着,他跑步、走路、爬山、骑,有时一天骑50公里。他知道,还有些东西没有达成,那股劲儿一直都在。
如果失去那口气,人生基本属于行尸走肉,刘奕君说,「你选择任何一种方式去生活都可以,但那些都不是最开始你想要的生活。」
在拍摄现场,没他的戏的时候,刘奕君喜欢闭着眼睛,其他感官因而像雷达一样张开。再远的地方,说到他的名字,刘奕君,或者刘老师,或者角色的名字,他告诉助理,该拍我了,他们在找我,你去看一下。助理说,没有啊。经常在这个时候,门开了,副导演进来,请他去走戏。
他说,他总是能听到。
「其实,我的内心是极不安分的一个人,谁也别想把我固封住,永远不会的,绝对不允许。」他说。
「这么多年,没有一瞬间想过真的算了?濒临想要泄一口气的时刻?」我问。
「没有。」他立刻回答。顿了下,他紧接着说了第二个,「没有。」像是确认某件事情,他持续地摇头,没有没有没有。
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天色昏暗,我们已经在暮色中谈了很久。忽然起风,尘土漫上来,附近白杨萧萧,声如涛涌。刘奕君声调愈发低沉,身体往椅背靠去。白色亚麻衬衫越来越皱,下摆在牛仔裤上堆成一团,此时你不会觉得他是个名人,他只是个普通人。只有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神态和身体都向前一步,没有,没有,没有。

5
36岁的隋意扬是一名斫琴师,以制作古琴为业,也是九嶷琴派第四代传人。他工作和生活在北京东二环护城河边的问渠书院内,2013年左右,刘奕君在书院与他相识。
第一次见刘奕君,隋意扬根本没认出来。他跟隋的学生一块来,藏在人群之中,几乎没开口。后来,刘奕君大多都是一个人来,穿着很随意的衣服,开着一辆很普通的小,悄没声儿地钻进院子。
隋意扬觉得,刘奕君喜欢问渠书院,还是喜欢这里足够安静,足够简单。这是和他身处的圈子完全不同的世界,那里吵闹喧嚣,热搜流量,一刻也停不下来。
书院则不同。这里住着隋意扬、他的师父和师兄三人,隋意扬做古琴,师兄画画,师父蜕山先生是书法家。每个人干自己的事儿,几乎不与外人接触。除了偶尔过过火,其他时候听不见任何声响。
院子的四季都好看。最高那棵是槐树,春天到处都是槐花散落。石榴、葡萄、柠檬、海棠栽满了院子,秋天会噗噗掉下三四十个果子。还有一小块菜地,种着薄荷、紫苏、香菜、菠菜、辣椒……刘奕君告诉隋意扬,真想有个这样的院子啊。
每次戏杀青了,刘奕君都会到这里待上一整天。听古琴,看字画,或者什么也不做。他说,书院和这里的人是他的还魂丹。遇上交付灵魂的角色后,来书院走一趟,能把他重新拽回去。
隋意扬记得,在王天风和谢侯爷霸屏的那段日子,刘奕君说,「一切都过去了,戏拍完,过去了,光环也过去了。」他告诉隋意扬,他想过,哪天没戏演了,就找个地方教表演。那时,他的人气刚刚爬上顶峰。
他也会宽慰隋意扬。制作一张古琴需要两三年,是非常漫长、孤独的工作。刚入行的时候,隋意扬经常入不敷出,最近几年才好些。刘奕君跟他开玩笑,「再过20年吧,一定可以的。」隋意扬觉得,刘奕君连计算成功的年份跨度都比别人要长,「20年」,只有听他说出来,才显得不矫情。
书院也来过其他的演员或名人,隋意扬都不太舒服,他觉得那些人都有一套标准化的语言和回答,毫无漏洞,似乎身上都有一个巨型气泡膜,提醒他不能挨得太近。只有刘奕君,他会打开自己的气泡膜,让人进来做客,「他愿意让别人觉得他是个普通人。」
但是,似乎没有谁能真正了解他。
华子觉得刘奕君是最不好谈的人。「如果特别容易谈的,他就是特简单的人了。刘奕君不是简单的人,他是一个最复杂的人。」
相识20多年,刘奕君从来没有跟华子吐露过自己的踌躇、纠结和不如意。有时,华子能感觉到刘奕君在自己跟自己较劲,自己跟自己打架,但他不会说出来。华子说,如果非要说刘奕君最大的特点,他会选择「隐忍」这个词。较劲,不甘,热爱,他都隐藏着,只有在表演时才会抖落。
刘奕君正在拍摄的新剧导演雷献禾告诉《人物》,现在的电视剧大多都是温吞水,刘奕君是那个能够把温吞水搅沸的人。「他一定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做了很多事情。而且他从不在生活中演戏,只在角色上演戏。」他说,很多演员身上的东西就像沙子一样流走了,但刘奕君身上有很多东西是留得住的。
荧幕上的癫狂与决绝,生活中的普通与内敛,「这就是他巨大的魅力,也是他巨大的让人不理解的地方。」华子说。
刘奕君喜欢点眼药水,隋意扬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觉得肯定是因为刘奕君平时眼睛费力比较多。他始终记得一个场景:他的一位学生来书院,想要跟刘奕君合张影,刘奕君那天穿得很随便,但没有拒绝,他说,「稍等片刻。」
他摘下眼镜,轻闭双眼,用拇指和食指揉了揉眉心,「啪」一睁眼,拍照的隋意扬手颤了一下,他定睛看了看镜头里的刘奕君,那是一个他平时从未见过的刘奕君,一个眼神比别人亮一倍的刘奕君。「他那眼神,全是故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