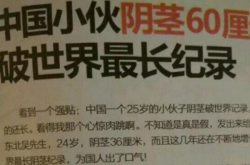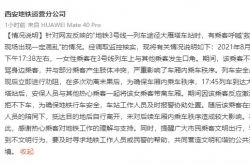一
我正埋头在办公桌前写资料,有人轻轻推门走进社工中心——这是一位身材娇小、头发半白的老太太,黄褐色的脸上盘织皱纹。她自我介绍叫袁信芳,今年快 80 了。她的诉求很简单:帮她找一家养老院,搬离与丈夫共同的家。
我在一处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做社工,专职服务社区里的老人们。这位老人的情况很少见,在广州,街坊有事会求助亲友,再不济,会找居委会解决。主动上门求助的,问题大都连居委会也无法调和。我和同事先安抚她,答应她,第二天会上门了解情况。
第二天,我和同事「明姑娘」登门拜访。袁信芳家在一处老旧的职工宿舍楼。居民楼靠近繁华商圈,楼下停满两排私家车。楼下嘈嘈嚷嚷,跳广场舞的阿姨们,大都穿着样式鲜艳繁复的裙子,和着音乐的节拍,慢悠悠地摆动胳膊和小腿。树荫下、树坛上,坐着老广州的叔伯们,有的眯着眼看报,有的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下棋。一些老人从菜市场回来,装满菜的小拖车一路上「咿咿呀呀」地响。住在这里的,大都是退休了的公务员、国企职工或教师,养老无虞,如果过得不开心,大都是精神上受了打击。
 袁信芳家附近的广场和街道
袁信芳家附近的广场和街道第三天,我俩循着地址找到袁信芳家,敲门三下后,袁信芳从锈迹斑斑的防盗门后出现,她脑后盘着的发髻一丝不苟,瘦小的身躯包裹在一身宽松的深色衣裤中。我们进了客厅,她又招呼我们在饭桌前坐下。
袁信芳给我们倒了水,自顾自地倾诉起来,主题只有一个:她要搬离这里,去养老院。因为她恨丈夫杨伯,认为儿子去世当天,他剥夺了自己见儿子最后一面的权利。
半年前,袁信芳 40 多岁的儿子病逝。「我儿子好『劲』 (粤语:给力、优秀)的。」她翻来覆去地讲,陷入回忆之中。
二
袁信芳的儿子叫杨潇,大学毕业后,在广州一处机场负责维修飞机。
当时,普通人坐飞机出游的经历很少,袁信芳也没有搭过飞机。一次,杨潇将母亲带到单位。她亲眼见到儿子的工作伙伴——一种巨型钢铁飞行器,长得像展翅的大鸟。老人至今也认为,那是一种神圣精密的先进设备,而儿子是能力者,拥有治愈这些钢铁大鸟的能力。
阿尔兹海默症夺走了袁信芳部分记忆,她记不得儿子是高级技工还是高级工程师,但这不妨碍她为儿子自豪。
不似妻子那么热络,杨潇的父亲远远地站着一边,不时看向这边。袁信芳留意到,恶狠狠回瞪他,他又沉默地转过头去。
说着,袁信芳带我们进了她儿子的房间。房间很小,木板床上凌乱地堆着一层薄被,一个孤零零的印花枕头,书架上塞满书刊,书桌上随意摆放的书籍上面蒙着一层灰尘,看得出,房间里的遗物依旧保持着原样,仿佛今晚主人就会回来收拾。
自从杨潇去世,半年来,袁信芳不准人动他卧室里的任何东西,她怕挪动位置,连将桌上物品拿起来擦拭都不肯。这不是我第一次见这样的老人,我曾拜访过一位丧偶的阿姨,她丈夫去世 1 年,出事当天搭在椅子上的衣服仍搭在原处。
儿子最后的时光在病房度过,袁信芳和丈夫轮流在医院陪护,她坚持每天煲汤,带到医院,大多数时候,袁信芳盛一碗汤放在杨潇床头,儿子艰难喝上几口后,无法再进食,那碗汤就放回原处,慢慢变凉,被父母喝掉,或者倒掉。
一个秋日清晨,袁信芳依旧在家煲汤。傍晚,她提着汤食走入病房,床上空空荡荡,她退出门外,想确认是否走错。方出房门,遇见家里的一群亲戚,对方告诉她:孩子没了,怕你伤心,你还是别去看了。
说话间,豆大的泪珠从她眼眶中冒出来。袁信芳用手背擦擦,抽了抽鼻子,隐忍着不哭出声来。我知道,她在用力克制,不想在外人面前丢分。但提到丈夫杨伯时,她开始歇斯底里:
「那个死男人,故意不让我见儿子最后一面。」
我留明姑娘下来安慰她,借口上厕所,出去找杨伯。杨伯站在屋外的走廊上,靠着栏杆,脸朝外抽烟,白色的蓬发在风中微微摆动。
我小心翼翼地搭讪,杨伯寡言少语,皱着眉头,用语气词回答我的问题,无法分辨他是在承认还是在敷衍。被问得不耐烦了,他伸手指指屋里,向屋内转两下头示意:「阿婆在屋里嘛,你去问她。」
我继续找话说:「阿婆好像很生气哦,一直骂你,说你不给她见儿子最后一面。这是怎么回事?」
杨伯掐灭烟,侧过身正对我,开始讲述杨潇去世那天他在医院的经历。
儿子走得突然,杨伯先通知了亲戚——原本应该先通知妻子,考虑到她有心脏病,当时又一个人在家,杨伯怕她承受不住出事,拖着不敢给她拨电话。几个亲戚赶来陪他料理后事,病房里一片忙乱,他也劝杨伯:「等她来了再说。」
儿子离世后,袁信芳止不住去猜想儿子临终时刻的种种。杨伯感觉,那天从医院回家后,原本就有认知障碍症的妻子的病情发展得更厉害了。她越来越记不住事,时常自言自语。夫妻俩本来就鲜少与亲朋往来,平日里只有儿子陪伴,现在,两人的关系因为儿子打上了死结。她每天长时间独自呆在儿子的卧室,想念儿子。她排斥丈夫,动辄就是破口大骂。
杨伯将此归因于妻子过度悲伤和认知障碍症。
杨伯认为,没有见到儿子最后一面只是妻子为倾斜情绪找的借口。最终,他同意让袁婆婆去养老院居住,只拜托我们,找养老院时帮袁信芳离家近的入住。
只考察了一家养老院,袁信芳当场定下床位。从养老院步行半小时就能回家。住进去那天,杨伯帮老伴提着行李,两人依旧没有言语。
袁信芳入住一周后,我去探望她。早上护工给她洗了澡,头发湿漉漉地散开,看起来很精神。她笑盈盈地带我们参观房间。
床上几件衣服叠了一半,护工说,她在这里无聊,每天都把衣服拿出来叠了拆,拆了叠。问她在这住得如何。袁信芳说挺好。
养老院并非封闭管理,可以请假外出,但袁信芳坚决和家里断绝往来。
杨伯舍不得和妻子失联,每隔十天半个月,会从家里煲好汤,带着汤来看袁信芳。袁信芳见了他就躲进房间,有时会边走边骂杨伯:「走啊你!」杨伯也不回嘴,每次妻子躲进房间,他就打开带来的保温壶,盛一碗汤放在客厅的饭桌上,在旁边坐着等。汤凉得差不多了,他起身叮嘱护工几句,朝袁信芳的方向说声「我走了」,便拎起空保温壶,慢慢下楼离开。袁信芳在房里知道了,不耐烦地说:「走就走。」从没有要送他的意思。
护工端来午饭,袁信芳喝几口汤,低头吃饭。护工看在眼里,忍不住说:「你老公对你不错啊!」袁信芳立即摆摆手:「那个人啊,不要提他了。」
对于失去至亲的老人,在家人陪伴下处理后事,出席葬礼,这是个告别的过程,有助于他们和缓地接受亲人离去的事实。在我接触的许多家庭中,人们出于保护老人的初衷,往往弄巧成拙。
三
像袁信芳这样的失独老人,在我的社工生涯中并不少见。2014 年 6 月,我们接报称,社区里有一名 23 岁的年轻人自杀去世,上面要求我们派同事跟进,对家属进行危机介入。
几天之后,快下班时,负责这个案子的同事阿华生气地说:「我早就叫他不要找记者的,他不听,现在好了,平白给自己找罪受。」
他埋怨的是 60 多岁的胡建培,那位自杀的年轻人的父亲。
儿子高二那年,胡建培的妻子去世了,他独自把儿子养大,后来,儿子考上省内一所知名大学。胡建培原本已经准备好 6 月份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孩子却因为考本校研究生落选,在宿舍用农药自杀,送到医院抢救了几天,还是不治去世了。
胡建培难以消化这个噩耗,认为孩子会自杀,是因为学校研究生录取过程有黑幕,愤怒地要打电话找记者曝光。阿华屡次劝阻,胡建培还是坚持找到当地一家卫视曝光,可没想到反而害了自己的儿子。
下一篇:有没有人后悔过生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