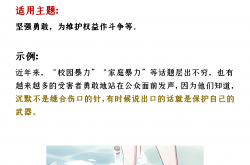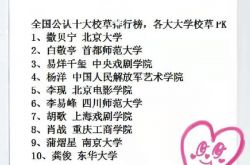2017年6月,我的表妹作为应届考生参加了高考。按她以往的水平,保二本冲一本不成问题。但考试的时候,她却发挥失常,最终成绩正踩普通二本的分数线,导致填报志愿非常受限。于是再三思索后,表妹选择了复读。
做出复读的决定是艰难的,但这样的艰难放在国内高考背景下,又显得微不足道。脱离苦海的执着改变着学生的生活参数,以至于那一年,表妹班上因身患抑郁症而休学,无法参加高考的同学多达五人,成为同届班级之最,一时间人心惶惶。
同学接二连三休学后,表妹告诉我:“要是这次考不上,我也不会再考了。”
以下是表妹的口述
1
2017年8月,我从市二高转学到市高,开始了复读的生活。
市高是整个市最好的高中,长辈们总说,能进市高读书,相当于半只脚已经迈入了大学。正因如此,每年都有许多考试失利的学生花高价插班学习,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复读的班级是尖子班。进班第一天,我就感受到了学习的紧绷感:60多平米的教室,日光灯永远开得像白昼一样明亮。课桌全以三小桌打横拼成一大桌的方式被分成三列,密密麻麻地分布在教室里。全班共有67个人,但教室里很安静,同学们都躲在半人高的书堆后面写试卷,时不时抬头瞟一眼黑板。厚厚的眼镜下面垫着几层卫生纸,防止托架压塌鼻梁。
我的座位被安排在教室左边贴着窗户的地方。为了让我坐进去,两个坐在外边的同桌必须得依次起身,曲腿,扶住桌子走出来,侧身在过道上给我让位置。等我进去后,她们再依次坐回去。
作为复读生,我很快进入了学习状态。每天六点起床来到教室背英语,课间背文综、写数学,累了就看看窗外的树杈,灰蒙蒙的天空和飞过的鸽子。每到这时,我总忍不住想:“明年这个时候,我会在哪里看天空呢?”想到这里,我又猛地摇头,让自己抓紧时间学习。
但我的动静很快引起了右边同桌彭佳的不满。
彭佳是当年的应届考生,据说她从初中一路披荆斩棘,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市高尖子班,一读就是三年。但越是这样的学生,对环境的要求越高。一次,我写练习题正写得起劲,彭佳左手肘猛地将我一推,使得铅笔在试卷上画出一道长长的弧线。
没等我反应过来,彭佳先开了口:“你翻书能不能别翻得这么大声?好像别人不知道你在学习一样。”我学习认真起来,确实容易把书翻得哗啦啦地响。于是我赶紧道歉,翻书也小心不少,但彭佳仍然三天两头冲我挑刺。
“你写试卷下面能不能垫本书,写得那么响,别人就不用学习吗?”
“你看题目能不能默读,非得读出来才满意?二高的毛病怎么这么多?”
彭佳的要求我都尽量遵守,但轻手轻脚地翻书、小心翼翼地写字实在让我难以进入学习状态。后来,我忍不住对坐在彭佳右手边的小满吐槽,说彭佳神经衰弱,这种小细节还放得这么大。没想到小满说:“彭佳以前不这样,但这段时间越来越敏感了。”
小满告诉我,彭佳的父母都是商人,开着市里最著名的连锁蛋糕店。优渥的家境让彭佳也十分好胜,想要冲刺最好的大学。但几个月前,彭佳的排名直往下掉,老师甚至在班上点名,提醒彭佳继续努力。“所以彭佳很着急,学习很用功,但是效果似乎不是很好。”小满说。
从那以后,我发现彭佳的努力真的超乎我的想象。高三的教室虽然是24小时开放的,但大多数学生还是会在晚自习后回寝室休息。
可彭佳却不一样。
彭佳是班上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人,随时随地都拿着一本英文词典背诵。听说彭佳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白天犯困时,就把胳膊拧得青一块紫一块,或用笔芯扎破自己的皮肤。到了凌晨两点还在喝咖啡复习。
但如小满所说,彭佳的努力没有换来成绩的进步。最近的考试,她又倒退几名,甚至比我考得还差。
排名公布的那天,彭佳趁我趴在桌上睡觉时,狠狠地踹了桌子一脚,我莫名其妙。后来才听说彭佳因为这场考试的失利,非常痛苦,甚至迁怒到其他同学,尤其是我们这种转学过来的人。但她对自己更狠心,冬季里,她睡觉连被子都不盖,以此惩罚自己。
可是,她的努力依旧没有成效。2017年末,彭佳开始出现反常。她总是一个人坐在座位上小声地嘀咕着什么,一开始我以为她在背诵或阅读,后来发现桌面上一本书也没有,仔细一听,是她在自言自语。不仅如此,彭佳和同学说话的次数越来越少,总是一个人闷着,或是一下下用头撞击桌子和墙壁。
这个情况引起了班主任韦老师的注意,她把问题向彭佳的父母反映,再把彭佳送到医院检查,得出了轻度抑郁症的诊疗结果。医生说,如果彭佳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症状不仅会加重,病情还可能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
于是过了没多久,彭佳就办理了休学,成为那届高三学生中,第一个因为抑郁症休学的人。
2
彭佳休学的事件在整个校园掀起了轩然大波,“万岁学长”的事又被大家重新提起。
“万岁学长”是2011年的考生。早在考试前,他的行为就有些反常,学校也建议他休学治疗。但学长的妈妈不同意,要求他撑过冲刺期,坚持到最后。学长也确实坚持下来了,但就在开考前几分钟,他突然精神崩溃,叫着“万岁!万岁!”跑出了校园,从此神经失常。
不久后,韦老师明令禁止同学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她认为这会渲染同学的消极情绪。“高考,不仅是知识水平的比赛,也是承受力、专注力、控制力的比赛。如果有人撑不下去,就会被淘汰。”韦老师站在讲台上摊开手说,“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无论如何,彭佳的事暂时被搁置下来,我和小满成了同桌。
小满的脸圆圆的,眼睛也是圆圆的,皮肤黝黑。她性格十分开朗,笑声响亮得像在瓮里打鼓,传出去很远。
那时,韦老师在班上实行高压学习政策,要求我们6点起床,6点半到教室,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其余时间全用来学习。一天写四五张试卷,还有各个县区的模拟题,每天都进行测验,困了就躲在书堆里小睡一会儿。当然,偷闲的聊天也是禁忌。尽管如此,小满还是常和我聊天,怕我承受不住压力,逗我发笑。
高压政策持续没多久,上次高考的失败感,和对未来的担忧像潮水一样向我涌来。许多次,我张开嘴大口大口地呼吸,却还是觉得胸闷。
一个闷热得快要下雨的晚自习,我把画满了叉的数学卷子狠狠塞进抽屉,终于哭了出来。我有点自暴自弃地对小满说:“完了,我感觉这次又考不上了。”
谁知那晚熄灯后,小满悄悄来寝室找我。我们一起躺在床上,她把一边的耳机放进了我的耳朵里。
我问她:“你把手机带来了?”带手机到校已经被韦老师明令禁止。但小满告诉我,她偷偷带来半个多月了,趁洗澡时用卫生间顶部的插座充电,她说:“我想睡觉前听听歌,缓冲一下。”
此后小满每晚都来,我们躺在黑暗里,有时听她喜欢的歌,更多时候是听音节毫无规律的白噪音。小满说:“我真想一头扎进深海里,就这么沉啊,沉啊,沉下去。海里安安静静的,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不用管。”
但这样片刻的缓冲并未能持续多久。一个早上,阿姨检查宿舍时,在小满的枕头下发现了她的手机,当即交到了韦老师手里。
而韦老师也立刻把小满叫到办公室,当着她的面把手机摔得粉碎:“这么关键的时候还想玩手机,你看自己最近考试掉了多少名?想要回手机就让你爸来领,这么不争气,对得起你爸吗?”
那天回到教室,小满的眼睛红红的,咬着下唇一声不吭。直到中午吃饭她才告诉我,这是父亲存了很久的钱才给她买的手机。
小满的家境并不好,父亲在水泥厂工作,母亲因为患有精神病,状况时好时坏,所以被关在家里。全家人的支出,都靠父亲微薄的薪水支撑。高二分班时,小满被分到了学校的尖子班,为了奖励女儿,父亲一咬牙,给她买了部手机。
“我当然知道带手机不好,一带手机,我的成绩就掉,把手机放家里,我的成绩又恢复一点,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住。”小满的眼泪大滴大滴地掉下来,“历史要点我背了五六遍都背不下来,抽屉里面的试卷,三天前就应该做完了,可是我的脑袋一点都转不起来,我着急啊!只有看手机的时候,才能轻松一点。”
小满举起手,用校服袖子抹了把脸,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3
那段时间,班里呈现一种奇怪的氛围,虽然只有沙沙写字、哗哗翻书和电风扇吱呀吱呀的声音,却总有令人窒息的高密度安静感。空气潮乎乎沉甸甸的,走进班里,就紧张得心跳失常。
为了帮同学调节心态,并让我们收获高效的学习经验,一个周五,韦老师特意把上一届考上中山大学的学姐请到班上给我们做动员。
学姐状态松弛,妙语连珠,一点看不出她也曾像我们这样整天油头垢面地拼搏。但学姐说,她曾因抑郁症退学,复读后才重新考上大学。
“我以前的状态非常紧绷,爱钻牛角尖,性格敏感。要是别人成绩超过我,我就会非常焦虑,看书要比别人多看两页,睡觉也比别人晚半个小时。”但学姐说这种自我感动的努力收效甚微,她号召我们戒骄戒躁,加强锻炼,让心态放松下来。
这次动员会后,许多同学都加入了锻炼大军。除了学校安排的常规跑操,我们每天傍晚也去操场上动两下。但只有刘畅不为所动,他还问我:“学姐怎么知道我看书的时候会焦虑,她是不是故意这么说,来讽刺我的?”
刘畅和我都是从二高转学过来的复读生,不同的是,刘畅去年因抑郁症已经休学一次,错过了高考,这是他的第二次备战。
但在我看来,刘畅并没有恢复得很好,他很少和同学说话,走路总是低着头,还经常斜眼偷看人。更要命的是,刘畅性格敏感,老觉得别人在讽刺自己,心中愤恨。所以和他说话,我总努力选择用词。
我告诉他:“学姐怎么可能针对你,她是说她自己也有这种情况。”刘畅不信,嘴里一边细碎地叨念些什么,一边低头走回自己的座位。
没多久,刘畅的情绪出现了一次小爆发。
那天我刚回到教室,就看到全班同学难得停下手中的笔,纷纷注视着刘畅。只见他站在位置上,指着前桌的女生大呼小叫:“我就知道你们背着我说坏话,说我是一个被命运宣判失败的人。”
女生仰头辩解道:“你神经病啊,谁整天说你坏话。”两个人争执了半天,直到韦老师过来,把他们都拎去办公室。
后来我们才知道,前桌的同学只是在讨论影视作品,并没有说刘畅的坏话。但他听到那句“一个被命运宣判失败的人”,就自己对号入座,才和同学争执起来。
刘畅似乎对自己是第二次复读,又是从二高转学过来的事有些自卑。他曾对我说:“这些市高的人总是瞧不起我们,我觉得他们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劝他:“大家都忙着复习,没这么多精力看不起我们的。”
但他仍然留心关注别人的讨论,生怕别人在背地里讽刺自己,连学习都无法认真起来。
刘畅的事情还没解决好,班里又出了事。
有天晚上,一个叫傅明的男生站到了宿舍的窗台上,被拉下来后当晚就被父母领回家看守起来。同学们说,他已经好几个月没和舍友说过话了,经常失眠了就站到窗台上去。考试不好就拧自己的胳膊和大腿,手臂上都是淤青。和他关系好的同学说,傅明经常自言自语说“考不上就完了”这种话,头抖得像弹簧公仔。
韦老师很快把傅明列为重点观察对象,并让心理老师对他进行了心理辅导。
4
“咱们班一连出了这么多事,你说咱们班是不是有毒啊?”几个引起学校注意的例子都发生在我们班,一时间人心惶惶。
学校也采取了措施,让心理老师给我们进行集体心理疏导,但效果甚微。仿佛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病毒,稍有不慎就会被感染,我的状态也越来越不对劲。
2018年初,我突然一点也不想复习了。就像脑子里本该有个引擎,按下电源就能启动思维,开动脑筋。但那段时间,发动引擎所需要的电池好像耗尽了电力。我早早到教室坐着,却只是面对试卷发愣。
周末妈妈让我回家休息半天,放松一下,我以复习为由拒绝了。但其实我起得比同学早,走得比同学晚,却连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我突然对很多事情都失去了兴趣,不爱说话,不想看书。分明知道时间紧迫——当时快到期末考,同学们几乎都跑步上学,站着吃饭,牺牲午休时间都要再写一套题。我知道再不努力,我的成绩又要下滑一大截,而且前几次考试,我的排名已经掉出尖子班了。但我的手却动不了,我的脑子对我说:“反正肯定考不上的。”看着身边努力的同学,我的脑子又说:“他们一定准备得很好,每个人都准备得比我好。我这么差劲,凭什么上大学?”
这种状态在我去年高考前也出现过,毫无缘由地消极、否定自己,最后考试果然失利。意识到这一点,我心里一片绝望,觉得历史又要重演了。
在这种封闭消极的状态下,我的期末考试果然考砸了。韦老师拿着排名表告诉我,中等班有同学几次考试排名都比较靠前,学校打算把他们调到尖子班来。
于是高三下学期,我从尖子班被刷到了中等班。
5
从二高转学过来的复读生里,只有我被刷下来,一时间感觉有些丢人,但中等班的氛围却让我有机会松弛下来。和争分夺秒的尖子班不同,这个班的同学常在课间去买零食、散步,要么在走廊上放松。我新认识的五个舍友也很开朗,平时几乎不聊考试的事情。我和她们打闹,尽力不去想考试和复习的事。
只有小满还是经常来找我。
她通常在晚自习的课间过来,蹲在墙角和我聊天,多数时候会倾诉最近的困难。
“你走之后,我在班里都找不到人说话了。”小满苦着脸说,“我的成绩有点滑坡,数学还有好多题型不会做,英语也找不到感觉,我好怕自己考不上。”自从小满的手机被摔烂,她的眼里就蒙上一层忧伤,说话声音很轻,我也再没听见她笑过。 
一开始我还鼓励小满,说这是黎明前的黑暗,从没听过尖子班的人考不上的。但后来,我对她的倾诉有了一些不耐——对我一个被尖子班刷下来的人,她哭诉个什么劲?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加上我交了新的朋友,花在小满身上的精力就更少了。
一个晚自习课间,小满又到班门口找我。彼时我正打算和舍友去小卖部,于是我们手拉手走到小满面前,我假装没看到她眼里的黯淡,神采飞扬地问:“我们刚好要去买零食,你去不去?”她直愣愣地看着我,摇了摇头。
“好吧,那我们晚点再聊。”
我就这么转身离开了,这变成了我高考后最后悔的事情之一——因为我的话,那天之后,小满再也没有来找过我。而我分明感受到了她情绪的极端变化,却没有在意。
2018年4月的一天,班里突然传来消息,尖子班四名学生被诊断出抑郁症,当天已经全部休学回家休养了。其中两个学生是轻度抑郁,两个是重度抑郁。令我吃惊的是,小满也在其中,此外还有刘畅、傅明,和另一个我不熟悉的同学。
接到消息后,我急忙跑到楼上的尖子班,发现小满已经不在了。我多方后打听才知道,这个学期开始,小满的情绪、状态和成绩就很不稳定。上个月,小满妈妈的病症复发,她一下子就崩溃了,确诊了轻度抑郁症。
6
小满休学那一天,我毫无保留地哭了一场。因为我没有及时察觉她的不对劲,因为我作为她唯一的倾诉对象,却又把她推开了。
由于妈妈生病的缘故,小满曾告诉我,她最大的愿望是将来能够学医。所以没人比我更清楚,她有多希望考上这个大学。但如今,想考大学的人被迫离开了,我这个注定考不上的人却留了下来,我既生气又难过。
这件事情之后,我脑子里的引擎好像又可以重新发动起来。我恢复到尖子班时期的作息:每天学习十多个小时,保持运动、补充营养,站在走廊休息时我也在背诵英文。不会做的题型,我一遍一遍地总结、练习,记不住的要点,我就多抄几遍。
我的脑子里偶尔还是会冒出“肯定考不上的”“尖子班的人这么努力,哪里轮得到我这个中等班的出头”之类的话语,但我也回答它:“考不上就考不上,但既然今年要参加的考试,我就要付出相应的努力才行。”
就这么不管不顾地往前走,那年高考,我竟考上了省里的一所211大学。
遗憾的是,考试结束后的聚餐和大一寒假的同学聚会,当初因为抑郁症休学的同学们都没有参加。过了许久我才知道,2018年1月休学的彭佳,因为状态恢复得还不错,又重新回到学校复读冲刺了,刘畅和傅明也是一样。刘畅的状态时好时坏,但他也在为第三次高考进行准备。傅明则插班进入了中等班,他父母不再期望他能考上多好的学校,只希望他尽力而为,考上一所大学。
而和我不熟的那位同学没再回到学校,小满也没再复读。
2018年底,我终于拿到小满的联系方式,又和她恢复了联系。休学后,她在家修养了一段时间,状态渐渐好转。现在她已经进入了一家私人中医馆,跟着老中医学习配药、制药、针灸等等。
我问她:“你不想再上大学了吗?”小满告诉我,她妈妈的病比之前更重了,经常一个人跑到街上骂来骂去,没人照顾是不行的。如果考大学,肯定要重新复读,就要多花一年的钱,再加上妈妈的治疗费,她爸爸一个人根本顾不过来。她觉得现在这样也不错,能学本事,还能照顾妈妈。
最艰难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考不上大学,这辈子就完了。后来发现,没考上,路也会继续。
小满说:“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之外,还有许多要承担的责任。”所幸人生中最漫长的那些日子总算过去,未来如拨云见日般清晰可见。
标签组:[升学考试] [高考] [刘畅] [彭佳] [傅明]
上一篇:《大江大河2》主演杨烁:抑郁时想过跳楼,父亲用爱拯救了我_手机网易网
下一篇:孩子得了抑郁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