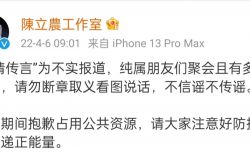发表自话题:明星大侦探结尾鸡汤

《明星大侦探》第六季在平安夜开播。
结果,节目却把里面出现的所有圣诞元素通通打了码。

网友们感到很纳闷,如果是要抵制过洋节的话,打码打到这种影响观感的地步是不是也太过了,大大方方一点没人会把你们怎么着呀。
还有人问,既然你自己都觉得圣诞元素可能会有问题,为啥打一开始你们不换个策划啥的呢,一定要用圣诞元素,然后放出来的时候就打码,大可不必。

其实,甭管这期节目出于什么考虑这么做,我们不能回避的一点是,节目担心的“敏感性”的存在,就是我们在文化上还处于劣势地位的一个重要体现。
而我们文化上的劣势,有一部分根源是长期以来,我们对文化建设就不是很重视,时代决定的。
网上关于中国人的语文是否在退步的话题,一直是被大家热烈讨论的。
早在2010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在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就指出:青少年汉语能力和汉字书写能力正在下降和退化。
前段时间,一份政府文件在网络走红,内容是“广西钦州市灵山县关于成立《武则天她妈在钦州》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组的通知”。

真是不知道是福是祸,偌大的中国,有几人知道广西灵山县?如今以这种尴尬的方式暴得大名,让人清楚了原来这里还有个武则天她妈的县,讽刺味道十足。
农村和基层的硬核标语,也常常在游走在文明尺度的边缘,早年是“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宁可血流成河, 不可超生一个”,如今变成了“隐瞒症状不上报,黄泉路上提前到”、“今年上门,明年上坟”。

碰到诸如此类让人哭笑不得的情况,很多人往往会说上一句:
你的语文是不是体育老师教的?
上过中学的都知道,语文历来是三大主课之首,看上去占据了沉甸甸的分量。
但真去看看补习班就知道,学英语学数学的挤破脑袋,学习语文和作文的门可罗雀。
语文在应试教育中成为一个鸡肋的存在,表面上好像是因为提分有限这样的功利性理由,背后却还有着重理轻文的社会风气。
父辈们口中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今天仍然没有过时,一直到现在,在大学里,学理工都还是主流。
结果,长期地重理轻文,种下了苦果。
走出国门,我们被全世界舆论围攻,毫无招架之力。
像女权、动保、环保、LGBT等白左思潮,以及后现代颓废亚文化在城市里落地生根,以至今天社会的割裂越来越深。

面对“人民富豪”们各种张牙舞爪,往无产阶级身上泼脏水,我们只能愤怒,或者调侃,写段子,玩梗,却始终拿不出一套真正的理论,对他们杀人诛心。
从“打工人”到“干饭人”,再到“小丑竟是我自己”,从劳资矛盾到感情问题,我们除了自嘲之外,似乎就没有办法了。

忽视以文科为代表的软实力建设,让我们国家,让我们知识分子,让我们底层劳动者,吃了很大的亏。
回顾历史,中国人在文理应该孰轻孰重的议题里,在以前就争论不休。
经历过几次大的教育调整,终于演变成现在的格局。
中国古代一直是重文轻理的,从夏商周的学习“六艺”,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四书五经”和“作八股”,不管是官办教育,还是民间书院,都以文科课程为主。
但这样也不对,科学技术总是落后于思想建设。
两次鸦片战争后,侵略者血洗中国,朝堂群臣被打醒,弄明白天天玩点诗书礼仪是没用的,洋枪洋炮才是硬道理,于是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开始了。

教洋文、军事和技术的新式学堂成了重中之重,对过去的思想有所冲击。
但旧帝国留下的包袱太重了,出国留学的学生们有的直接剪了辫子,回来后不仅在人群中贻笑大方,甚至还会被砍头。
走马观花,上房顶揭几片瓦,换一身新式官服,就到了民国。民国面对的世界形势更复杂,国外一战打响,国内铁骑践踏,带有强烈反思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那场中西文化论战开没彻底结束,1923年中国思想界又掀起了一场大波澜。
搞哲学的张君劢,在清华给出国留学生作了一场名为《人生观》的演讲,说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他的朋友地质学家丁文江对此非常不满。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文章反对张的观点,字数是他的三倍还多。
这一下就热闹起来了,文科理科两大阵营的学者,纷纷撸袖子上阵,有的支持张君劢,有的支持丁文江,这就是著名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简称“科玄论战”。

在新文化派眼里,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大师胡适就是这派的领袖,他说:“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相信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
老一辈的学者们对此不以为然。
1920年,梁启超游历完欧洲回国,他见识了欧洲战后的破败景象后,就在他的《欧游心影录》里发出了感慨,说“科学万能之梦”已经破产。
梁簌溟对科学也有警惕,认为科学本身就含有有害的生命观、粗糙的功利主义和过度的行动主义,要对它加以必要的节制。
科玄论战没有彻底定下胜负,但它开启的文理之争,却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所留下的思辨,也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此时,教育系统的人大多还是文科出身。
1921年,东南大学招生考试中,有一份国文卷子令老师们交口称赞,评卷后,老师们都打了满分。这名考生名叫卢冀野,年仅16岁,号称金陵才子。
卢冀野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他有首小诗,在今天广为人知:
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
后来一句“梦里花落知多少”,还被作家三毛拿去做了书名。

不过,卢冀野此次并没有被录取,因为他的数学是零分。
第二年,他卷土重来,数学成绩还是不行,但国文系破格将他招录进来。
民国时期跟卢冀野一样被破格录取的人相当不少,作家钱钟书数学15分,进了清华;著名力学家钱伟长,数学、物理、化学和英文加起来25分,进了清华;历史学家吴晗数学零分,也进了清华。
看来今天所谓“高校自主招生灰色寻租空间”的问题,在民国就已经大行其道了。
毕竟偏科到这种程度还能混进清华的人,家里也都是有头有脸的名门望族。如果你操着一口湘潭土话,穿着上衣衫褴褛,那些大教授、大知识分子们,想必是不会多看一眼的。
民国的文科教育,一种是农村地主乡绅举办的传统学堂,学的是诗词格律和四书五经,从古人的著作里寻章摘句。
另一种就是这种新式教育,但它是以美国为老师的,连清华大学都是美国经费支持的,更不用说许多教会大学了,他们学习的自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思想理论。
不管是老掉牙的封建杂学,还是匍匐西方的新学,都不符合时代的需要。

1927年,国民政府迁至南京后,创立了中央大学,并对中山大学、浙江大学进行改组。这一时期,受到重点支持的大学,学术研究都偏“理工”,主要是天文学、地质学、农学、生物学等相关学科。
这时候开始,大学理工科逐渐开始吃香了,学生普遍重视英语,就是为了方便学习西方科学技术。
1932年5月19日,广州的教育专家在中山大学召开了一次讨论大学教育方针的会议。会上达成了一个议决案,其中第一条即是:“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同时多设职业学校,以适应社会生活之需要。”
很快,国民党中央也响应了。
陈果夫提交了一个所谓“彻底改造教育之新动议”,里面指出,“自本年度起,全国各大学及专门学院,一律停止招收文法艺术等科学生,暂定以十年为限。”

陈果夫的提案还没到达中央,学者蒋廷黻听到消息后,赶紧在《独立评论》上进行了“不必评论”的评论:“国家怕乱就把这些功课停了;停了的结果徒然使国家更加乱,因为国人的思想更加会乱。”
民间反对声不绝于耳,政府强行推理科教育,收效甚微。
民国的教育虽然重文轻理,但由于没有主体文化和指导思想,歪理邪说泛滥校园,唯心主义泛滥,很多所谓的大师,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并没有为国家创造出一套系统性的理论。
更重要的是,民国奉行的是精英教育,城市资产阶级搞新式教育,农村地主乡绅搞传统教育,但广大群众几乎都不识字,上层和下层各玩各的,这样的教育注定是失败的。

毛泽东曾说过,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文化。
解放战争尚未结束时,扫盲工作就已经开始了。解放区每到冬天农闲季节,农民们便被组织起来读书识字。这种学校只在冬天开课,因此被叫做“冬学”。
新中国规模更庞大的扫盲运动,使广大人民摆脱了旧社会的噩梦,打开了知识文化的大门,从而实现了自身的解放。

但由于我们国家选择苏联阵营,在高等教育上却是做出了 “以俄为师 ”的战略抉择 。
苏联教育模式是一种专才教育,依附于计划经济体制。学生招生和分配完全根据国民经济建设计划学科是否存在和专业细化的程度。
最高学府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只有两个专业,经济系只有三个专业,而农科达90余种专业,工科专业更细化到200多个。
建国前夕,1949年9月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就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农业、工业和国防建设。
1952年至1953年,中国教育部仿效苏联高等学校,调整出大学中工、农、医等“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的学科,新建专门学院或合并到已有的同类学院中来重点发展。
这就是著名的“院系调整”,也就是把原来的综合性院校,拆分合并为专科院校,比如清华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工科院校。

院系调整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被停止和取消。拿社会学来说,原来分布在全国的20多个社会学系经过1952年的调整,只剩下两个,1953年院系调整后,仅存的两个社会学系也被取消。

院系调整的弊病暂时还没体现出来,因为那时在革命话语的主导下,而且那个男人也还在,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担当了整个中国思想文化输出的重任。
那时候,全世界左派知识分子都向往着中国,中国是他们心中的圣地。萨特和波伏娃来到中国,呆了整整45天,甚至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大典。
另外一方面,以当时中国一穷二白的国情。别无选择,只能选择搞规模化的工业化教育。
在这样的教育系统中生产出来的海量工程师,被投送到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中,短短三十年不到,就建立起了现代化工业基础。

而这波社会主义的遗产红利,中国人至今都在享受着。
应该说,建国之初以理工为导向的教育培养方式,是正确的,合理的,也是成功的。
到了八十年代,当我们国门打开时,人文领域的薄弱问题体现出来了。
新旧交替的时代,革命话语被猝然放弃,自己的体系又没建立起来,学生们越来越迷茫,潘晓那封著名的来信,说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在同一时间轴上,中国尚好,苏联的结局就比较悲伤了。
曾经耀眼的强国早就埋进了历史,今天的人评价起苏联末期的时候,可以说他腐败沉沦,可以说他穷困潦倒,可以说他耀武扬威,但没能会说他科技不行。
放弃了阶级斗争和革命输出的苏联,旧势力的内部侵蚀,知识分子们被收买,整个国家的软实力崩塌,导致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最后完完整整葬送。

八十年代以后,中国仿照美国进行教育体制改革,从教材审定、教学大纲到课程体系,全面学习美国。
西学的冲击从未像当时那么大,面有饥色的中国人民被莺歌燕舞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撞了个满怀,知识分子也很快为西方学说所折服。
以至于河殇之流一度占据了官方意识形态,很多年后,河殇派的徒子徒孙们还在互联网进行他们最后的冲击,用一些子虚乌有和蹩脚低级的段子,把人心搞得惶惶不安。
乃至今天,左右之争仍是如此激烈,如果不是网民普遍开了眼界,西方国家又频频暴露马脚,你很难想象舆论形势会是怎样。
很多人觉得,只要够硬够强,别人就会心悦诚服。
但有时候,敌人可能是周癫,“我打不过她,但我就是不服不行吗?”

半截身子入关的苏联,就因为软实力不够,长期处在舆论下风,连带着连硬实力的形象都受损了,搞得现在都有很多人觉得苏联人常年吃不饱穿不暖。
封建时代的农民长期被地主阶级剥削,即便有反抗的意愿,也始终逃离不了儒家思想忠君爱国的桎梏,最后被视作流民和草寇。
近代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提供了法理依据,但中国那时并不是资产阶级统治,农民也不是无产阶级。
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把农民划分到无产阶级里面,把推翻三座大山视作革命目标,这套总政治路线就是革命成功的合法保证。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问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对不对,中国人喜欢讲一个“理”字。
说到底,这是要一个合理的保证和解释。
那么这时,需要的就是批判的武器,而不是武器的批判。
今天我们知道西方国家话语的虚伪,知道那套新自由主义理论是糊弄鬼的,但我们仍然不敢放弃使用“民主”和“自由”这样的词。

因为这套话语和意识形态不是美国霸权决定的,而是几百年西方思想的积淀。
它们有莎士比亚、歌德、梭罗、海明威这样的文学大师进行抒情叙事,有霍布斯、孟德斯鸠、洛克、伏尔泰这样的思想家建构政治理论,有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创立底层理论。
当西方的国家杀人放火、攻城略地、惨无人道时,依然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地从里面找到各式各样的例子和思想辩护。
连中国人在写文章时,所用的名言警句,也不得不从里面摘录。
很不幸,当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时,只能借用他们的,或是粗制滥造进行二手包装凑合使用。
这就好比你拿着刚出新手村的丐版武器去和满级装备的西方国家打,这怎么打得过呢?

遗憾的是,很多工商业发达的地方,原本应该努力在文化建设上也敢为人先,但他们似乎对此不感兴趣,反而开始兴起复古浪潮,从历史坟墓里攫取废渣。
不是什么称赞乡贤,就是什么争当贵族。

早在1965年,美国颁布的《高等教育法》里,就指定了美国几所大学作为国家东亚资料中心,这些智库源源不断地为国家提供决策支持。
2003年1月21日,美国在原先新闻办公室、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基础上,新成立了一个“全球传播办公室”。
在伊拉克战争中,这个办公室煽动了一场媒体之战,统一协调白宫、政府各部门和军方的口径,美军侵入伊拉克的行为,明明是一场侵略战争,结果就被一致定义为“解放战争”,而且保证政府和军方系统能对“全球24小时的新闻播送”所提出的质疑和批评给予最及时的回应。
日本同样如此,日本开设了多个专门研究机构,其中有个叫三井物产的公司,信息收集能力被认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之上,它设有专门研究中国的部门。
三井物产在中国设有17个点,遍布全国,东至青岛西至成都,北到呼和浩特南到香港。
他们关注中国的“一带一路”、中美贸易、新能源汽车政策动向……

甚至连印度,都有自己专门造谣攻击中国的舆论机构。

革命话语已是久远的记忆,西方价值在此水土不服,所谓特色社会主义解决的只是经济政治层面的问题,在解释中国自己的体系时,我们的思想领域还远不够强大。
是时候重视以文科为代表的软实力建设了,现在众人皆醉我独醒,全世界都浑浑噩噩,一塌糊涂,正是进行文化输出的好机会。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是一种力量。
行文如刀,笔墨诛心,杀得人退避三舍,也是一种力量。
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只会“我全都要!”

参考资料:
《重理轻文:高等教育“师苏联”的教训》网易新闻
《科玄论战:先声与往事》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文理之争:民国时的一次教育大讨论》学习时报
标签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