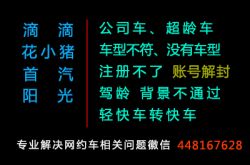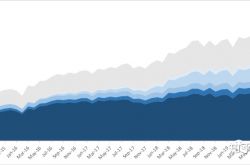发表自话题:蒋方舟日本
原标题:蒋方舟:我为什么要主动脱离社交网络?
原创: GQ Talk GQ报道

智趣多元的声音杂志,一周一会的声音派对,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GQ Talk。
三个月前,蒋方舟开始了一场“互联网脱退实验”。简单来说,就是尽量减少上网和使用手机的时间,不刷朋友圈,不关注微博热点,不加入微信群,不在网上跟人探讨问题,尽量用面对面交流取代微信聊天。
如今,互联网似乎已经跟水和空气一样,成了日常生活的基础条件。智能手机成为手臂的延伸,几乎成了一个不可剥离的身体器官。社交网络上的文字、语音和表情包正在逐步取代面对面的交流。在蒋方舟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事情。她决定用脱离社交网络来表达自己的态度。
蒋方舟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三个月的实验,效果如何,她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在由NEX联合呈现的GQ Focus「新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主题活动中,蒋方舟讲述了“互联网脱退”的具体感受。
为何公共舆论空间中的议题被讨论的程度和它们的重要程度不成正比?为何网络空间成为言语暴力滋生的绝佳场所?我们上网的目的是否逐渐变成了一种不自知的自恋?社交网络是否让我们丧失了与人面对面交流的能力?在演讲结束后,我们又与蒋方舟探讨了上述种种问题。
我为什么要主动脱离社交网络
这个演讲源起很简单,当时何瑫老师看我发的一条朋友圈,配了一张自拍照,照片里我在用钢笔手写作,说我已经不在互联网冲浪了。我在最近几个月写作大部分变成了手写,我的互联网脱退实验还包括我基本上不关注任何的热点事件,跟人的微信沟通基本上保持在最小和最基本的频率里。

先讲讲我互联网脱退的动机和方式,第一,就是我不再关注互联网上的热点事件。今天我们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从微博热搜,有一些话题确实承载了一定的公共性,但这种公共性其实是非常微妙的。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从一个男明星让她的老婆推行李来看夫妻之间的权力结构和现当代中国女性在婚姻当中是不是处于下嫁的情况,还有女作家的马桶失灵戳破了上流的幻想,今天我点进去一个热搜,讲一个阿里P8的员工征婚,折射出中国婚恋市场的极度不平等和人们对于婚恋的种种幻想,诸如此类的话题。
我并不是说这些话题不具有公共性或者不值得讨论,但是我觉得它们被讨论的程度是不合比例的。这种不合比例有两个层面,一个在于它的受关注度,其实它们本质上都是一些私人的事情。大家在生活中都非常讨厌被七大姑八大姨来打探自己的隐私,但在互联网上大家变成了非常积极地去打探隐私的人。我们对于私人话题的关注会被变态地放大;当我们发现很多公共议题不好展开的时候,对于私人领域就会超乎寻常的关注。

另外一个不合比例是严肃性的不合比例,或者所谓公共性的不合比例。因为无论我们以多时髦的词汇、多专业的名词、多长篇大论的文章去包装它们,它们本质上就不是严肃话题,本质只是一种个人选择,并不承担足够的公共性和严肃性。
我们严肃地讨论它们的唯一效果是我们看起来很严肃,不是单纯的七大姑八大姨了,看起来像一个讨论社会事件的社会人一样,但是无论我们看起来多严肃,都无法掩饰这些话题本身的琐屑和私人。
因为这两个原因,我基本不再关注任何互联网热点。
其次,我之所以开始实验互联网脱退,是因为我发现网络暴力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我开始思考为什么在互联网上人和人之间好像失去了尊重。其实我觉得原因很简单,因为尊重其实需要距离,但是互联网所做的就是祛魅,就是让距离感消失。
尊重需要距离,但是暴力不需要距离,当一个人变得没有距离感的时候,变得像是你身边的人一样的时候,你是最容易滋生对他的网络暴力。有时候我看到互联网上成千上万的人大肆咒骂的、人肉的对象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而是更像我们生活里常见的坏人,恰恰因为他和我们的距离并没有那么的大,所以成了仇恨发泄的对象。
所以我互联网脱退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对于网络暴力我觉得难以理解,很多时候并不是痛恨,而是会觉得有些不解。除此之外,这种距离感的消失滋生了一种自恋。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前两年的时候我跟一个女明星一起做了个节目,节目她表现得很自信、独立、刚强、潇洒,而我就表现得很猥琐,很想谈恋爱什么的。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猥琐,但现在很流行那种捧一个踩一个的话术。那段时间我看到了大量微信自媒体的文章,我朋友会转发、截图给我,我觉得很好笑,标题都是“我们都想活成XXX,最后活成了蒋方舟”,“每一个男人都想娶XXX,但最后还是娶了蒋方舟”。我看了之后觉得很好笑,好像已经在脑海里把我许配给了一个又一个不知名的程序员之类的。
后来通过这件事,我发现了这种自媒体文章的话术,它让每个它提到的人都联想到自己,都让你觉得这就是我,我们看到大部分10万+文章要么引起焦虑,要么引起共鸣,其实焦虑也是共鸣的一种。我在互联网上最害怕看到日剧或者综艺节目的台词截图,密密麻麻几万转发,每个人都在说,“这就是我”,“说的就是本人”。


那到底要不要恋爱呢?
当然我完全能够理解每个人都试图从他人的生活当中找到自己,但这是不是我们上网的唯一的目的呢?我曾经跟我一个互联网创业的前男友吵过一架,当时他说人们上网的目的就是为了虚荣,就是为了让别人来称赞自己,我当时并不认同,可是现在似乎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每个人都在他人的言语、生活、经验、表现当中去找到自己,无论这个人是个明星、名人还是虚构的人物。
我觉得自恋其实并不可怕,但是我在想的是,一个膨胀的自我是没有能力关心他人的,我始终觉得人的灵魂好像在我心目当中有个非常具象的形象,人的灵魂是有限的,当它充满了对于自我的关照、怜悯、同情、爱惜的时候,他有能力关心他人吗?
现在我也尽量在自己的文章里面去少表达我也是你,我也是你们,我也走过跟你们一样的路这样的逻辑。我觉得引起共鸣确实是一种非常投机取巧的获得所谓的热点和互联网关注的方式,我觉得作为互联网从业者,媒体人,我们是不是应该从自己开始做起,少一些对于他人自恋的唤醒呢?

10万加爆款文章用来引发共鸣的高频词汇
我互联网脱退的另一个方式,就是不再参与任何互联网上的争执和讨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互联网上话语圈的撕裂越来越严重,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小到婆媳问题,大到公共话题,互联网上几乎每一个问题你都可以看到人们迅速的分成了一拨和另一拨,然后相互撕得不可开交。
我们话语圈的每个角落似乎都形成了一种敌我关系,好像饭圈文化已经演变成了公共舆论的主流。每个话题都好像是一个idol,然后在这个idol周围的是核心的粉丝,粉丝的周围是我们要制服、要驳倒的另外一群人。话题没有灰色地带,要么就是挺我,要么就是黑我,只有这么两种状态。我们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东西的接受度变得越来越低,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几乎不在网上跟人讨论任何问题,因为我觉得任何问题到最后都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游戏。
我的互联网脱退实验的最后一点是,我尽量减少跟人在微信上面的交流,基本上只说一些事务性的事情。因为我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这个故事是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讲的,叫做聪明的汉斯。汉斯是匹马,这个马很神奇,人们发现它有一个特殊的能力,会做算数,你问3+5等于多少,它会用点头或者点蹄子的方式告诉你是8,几乎从来没有失手。

聪明的汉斯和它的主人
这个马没有特异功能,也不会算数,它怎么得出正确的数字?其实也很简单,它敲击马蹄的时候会根据现场的反应判断哪一下该停止。当它快得出正确的答案的时候,它察觉到看它表演的人的氛围发生了些许的改变,大家开始紧张点头、窃窃私语,它就不再敲击马蹄。
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故事,它告诉我们真正的交流是什么,真正的交流是非常微妙的事情,它包括每个人的语气、表情和停顿,空气中的味道,这一瞬间的凝固的感受,这是真正美妙的交流。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可悲,马都有一种所谓的交流的能力,但是好像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正在逐渐地丧失这种能力,我们丧失了对别人肢体动作的解读能力,渐渐地自己也不会通过一些微妙的表达来传递自己的想法。
我有个好朋友,我很喜欢和他聊天,每次我都要给他出打车钱让他到我家里来跟我聊天,请他吃完饭以后再给他打车的钱回去,这是非常费钱的事情,但是我就是不愿意在微信上面和他聊,因为我觉得一个畅快的交流其实包含了交流双方非常全面的一种互动,而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技巧。
我最喜欢的一个关于文学的故事,是契诃夫的小说《吻》,故事很短,讲的是一个很丑的士兵,有一天在黑暗中被人吻了一下,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被人吻,他很高兴,跟人去讲这个故事,他以为关于这个吻能够讲一天一夜,但是没想到不到一分钟就讲完了。
我在想,之所以要有文学家,之所以要有小说,是因为小说是无比美妙的延长时间的一件事,在小说里,一个吻可以有一个世纪那么长,因为它可以把一切微妙的东西全部表现出来,这是美妙的交流。但是很遗憾,无法在线上实现。

所以当我讲到的我的互联网脱退实践的时候,有人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矫情,少上点网或者给手机设置一个屏幕使用时间就行了,但是其实我觉得并不是那么简单。保持无知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今年我没有看过一个综艺、一集电视剧,但是我就知道盘尼西林被打了,脱口秀大会的冠军是谁。
我不知道我是如何获得这些信息的,很奇妙,他们渗透进了我的大脑,所以在这个时代保持无知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有的时候你甚至需要去强制自己脱退,甚至是不太愉快的脱退,你才能够保持无知。
人为什么要保持无知呢?因为我经常把大脑想象成一个空间,当我们的居住空间大了,有很多我们并不想要但免费送上门的烂东西的时候,我们知道要么上闲鱼卖了,要么就扔掉,我们懂得对具体的事情去断舍离,但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对头脑当中的空间断舍离,当我把头脑里面的空间断舍离的时候,才能让自己的脑袋里装进更多的东西,这就是我有些变态地去强制自己脱离脱退互联网的原因。
我去看了李安的新片《双子杀手》,他在电影里克隆了一个年轻的威尔·史密斯,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威尔·史密斯是非常完美的杀手,当你见到这么完美的杀手的时候,你很难拒绝这种诱惑,你要再克隆一个完美的他。李安为什么要坚持120帧的高清拍摄?他给的理由也很简单,当你能那么清楚地在大荧幕上看到东西的时候,你很难拒绝诱惑。
只要手机在身边,只要浸泡在社交网络里,我们的生活就时刻都在经受诱惑。当你上了一次热搜的时候,你就想天天上热搜,当你写一次10万+的时候,就天天想有10万+,你很难拒绝这种诱惑。如何去抵抗诱惑呢?王尔德说,除了诱惑我什么都可以抵抗,但抵抗诱惑最好的方式就是臣服于它。
但是我不同意王尔德,我觉得臣服于诱惑之前,我还可以坚持一会儿。
蒋方舟的演讲结束后,我们又与她继续探讨了相关话题。
我们并没有陌生人社会的传统
傅适野:说到日常交流,你在演讲里也说到你现在更重视的是线下的,而不是微信上面的交流。你会觉得面对面的交流可能会更生动,更加有细节。你讲到说你有一个朋友,你给他出打车钱来你家聊天。
蒋方舟:对,我就斥巨资,50块钱打车费,来回100块钱巨资,邀请他来聊天,可能到我们家附近的咖啡厅,或是一起吃个饭之类的。我在微信上面聊天,我总会有一种时间的紧迫性,因为你看不到对方的这种表情,所以你总觉得对方马上要去忙了,或者怎么样,始终是处于一种非常不安的状态当中。
你不知道这个谈话能够持续多长时间,而且你不知道这个谈话在对方心中的份量,所以大家只能采取一种最浅的方式去交流,我不太喜欢这种交流,因为我会很不安,而且我是一个特别害怕耽误到别人的人,所以我发现自己没有办法长时间在微信上面聊天。我自己的工作量很不饱和,别人都是要上班的人,聊着聊着我觉得你是不是要去忙了之类的,我就不太喜欢这种聊天的方式。
而且我经常会觉得现在人们不会聊天了。那天我还在跟朋友说,为什么我们很难拍出像日本《深夜食堂》那种场景的电影,因为我们并没有陌生人之间说话的习惯。甚至你去餐厅看两个朋友或者是一对夫妻、一对情侣吃饭,也都是各玩各的手机,你会发现其实大家都不太会聊天了。

日本还有一个综艺节目挺火的,就是在路上随便找路人,就跟着到他家去,了解他的人生故事。这好像在他们的文化里面没有那么突兀,还是有一些陌生人之间的情感关联在。而我们并没有这种陌生人社会的传统,我们很难去设想一个场景,比如说在酒吧,两个不认识的人就开始生聊。如果有人跟你们这么聊,你就会觉得聊一聊对方就要给你推荐小额贷款,或者说我爷爷是卖茶叶的之类的。
张之琪:其实我们也没有这样的空间,比如说像国外有很多公共空间是可以让你发生这种相遇的。
蒋方舟:对,比如说我之前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在一个酒吧,那个开酒吧的人会做一些简单的食物,会跟每一个客人聊天,这个人很有意思。不是他个人有意思,是这种文化有意思。他每天会看报纸,因为日本人还有看报纸的习惯。是为了去找能够跟客人聊的内容,他是为了他的职业。
在国内,如果一个酒保和你聊天,你会觉得被冒犯到,或者会觉得,你是在撩我吗?或者说你是在拍快手吗,拍抖音吗?你就会有警戒心,而且你觉得这是一个不日常的场景。
傅适野:这个也挺有意思,在外人看来日本是一个高度现代化、原子化的社会,但实际上他们的交流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蒋方舟:我们都说日本或者很多其他大都市是陌生人社会,但是没有人真正能够在一个孤岛上生活。陌生人社会也会发明很多陌生人之间萍水相逢式的交流方式,陌生人之间情感连接的一种方式,它其实有一种特殊的陌生人交往模式。但是在中国,我们从大家认知当中的一个乡村式的熟人社会,快速进入到了社交网络所分割的人和人的个人空间当中。我们其实没有去建立线下的、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的陌生人之间的这种相处模式的机会。
张之琪: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好像是更先进一点的,比如说我们特别依赖电商,移动支付,特别依赖移动互联网。但其实是因为你中间那个漫长的过程被跳过去了,当大家刚开始形成一个消费社会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电商的阶段,所以就导致中国的零售业非常差。你上街其实买不到什么东西。
蒋方舟:就是因为我们用非常短的时间完成了别人在十年或者是三十年或者一百年发生的变化。磁带和唱片在国外持续了非常久,它的衰亡也是非常缓慢的,而不是像我们可能一夜之间就会发现一个产业、一个工业或者是一种美感,就不存在了,你再也找不到了。我们用非常快的时间完成了别人用很漫长的时间发生的变化,这确实是有好有坏了。
当不消费成为唯一的武器时,我们有点虚弱
张之琪:你提到网络话语非常撕裂的一个原因是很多时候网友抱着一种消费者的心态,用购买的行为代替了协商或者对话行为。但这个可能也不是互联网特有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消费者这种主体性,或者这种身份已经覆盖了我们其他所有的身份。你在干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都是消费者心态来做决定,做选择,做表态。你在生活里有这样的体会吗?
蒋方舟:有啊。我觉得我最早感受到这个是2005年的《超级女声》,当时我身边很多朋友都非常兴奋,因为可以用投票决定选手命运。你会觉得这是一种权力关系的转换:遥控器在我手上,这个选择权在我。
但我也在反思这一点,是不是有钱能够买东西的消费者身份是你唯一的立身之本?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挺可悲的,因为你会发现很多对抗的方式就会变成,那我不买你的,我选择不消费,以不消费的方式进行对明星、对观点、或者对任何东西的抵抗。

蒋方舟:当不消费成为唯一的武器时,我们是有点虚弱的,或者这个武器是不够的。
张之琪:这个事情其实挺令人沮丧的。除了消费者之外,我们还能不能是别的身份?
蒋方舟:对,这好像是我们唯一拥有的权利,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挺可悲的一个事实。
张之琪:而且你刚才提到,在超女的时代,如果你想多投一票,你得多买一个手机号才可以。但现在就不是,你充一个会员,或者你买一个什么东西,你就可以比别人多99票。你越有消费力,你掌握的票就越多了。
蒋方舟:对,所以你会发现当消费变成核心的时候,在所谓的亚文化领域,就会细分成最有购买力的人就是最核心和等级最高的消费者,其他你所掌握的权力和话语权是根据你的消费能力依次递减的。说白了这就是很势利眼。而且反射到被你消费的对象身上,他身上聚集的购买力越多,他也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
张之琪:这个其实也可以回到你刚才讲的KOL,他们的观点越来越小心翼翼了,是因为他其实输出也是一个产品,他希望别人能买。如果这个产品,也就是他的观点是冒犯性的,那他的市场就有限了,所以大家都是有一个讨好的心态在里面。
蒋方舟:其实真正有价值的观点,我觉得一定是有一些冒犯性的。他一定会冒犯到一些人,因为它会挑战人的固有认知,会让人有一点不舒服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观点可能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喜欢挑刺,逐渐地就消失了。他在说之前会去先权衡一下这个观点,环保的人会不会不喜欢,女权主义者会不会不喜欢,虎扑直男会不会不喜欢。
而当你权衡了所有的观点的时候,你得出来的就是一个无聊的观点。并且会养成一个习惯,时刻去维护这个观点,所有的观点都是以这个东西作为一种延伸,所以就形成了人设。
张之琪:你的互联网脱退实验做到现在,想把它继续下去吗,还是说你觉得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实验?
蒋方舟:会继续下去,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现充”,就是现实生活很充实的人。你只有做出这种选择之后,才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去有意识地去培养你跟他人的关系,去寻找虽然不那么热点,但是你觉得有价值的内容。我觉得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才能够去开始人生下一个更好、更丰富的一个阶段。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还是挺愉快的。
本期节目由NEX联合呈现
智趣多元的声音杂志 一周一会的声音派对
GQ Talk
我们下期再见
制作人:傅适野
主播、撰文:张之琪、傅适野
监制:何瑫
运营:肖呱呱
阅读原文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