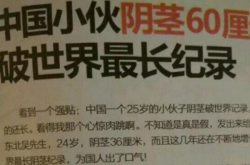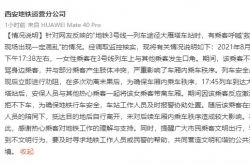发表自话题:512的暗示


编者:今天是护士节,在这个与生命、与人间大爱息息相关的节日里,历史上的今天又发生了什么?是一场大灾难降临人间,无数条鲜活的生命在灾难中瞬间消失,无数个幸存者在失去亲人后撕心裂肺、肝肠寸断......我们不会忘记,13年前那场不堪回首、骇世惊天的5.12汶川大地震,随之,悲痛、悲壮、感人、震撼同时发生。大灾、大难有大善、有大爱,泱泱大国"众志成城,抗震救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场与死神的殊死搏斗迅速展开。一曲人性关爱的悲壮序曲瞬间奏响。让我们随同叶晓藜战友的“北川行”,再次感受那场人间大爱!
——写在地震百日祭
【一】
这座城,死一般的寂静……
这座城,曾经美丽惊人的一湾湔水,依然静默蜿蜒,曾经嬉戏湔水中的一脉青峰,依然游龙驻足,曾经蛇行进城的“Z”字大道,依然横卧青葱山坡,只是湔水多了秽物,游龙瘦了身形,“Z”道积满了沙砾粉尘……
穿行在这座城,骄阳似火,却没有焦躁的蝉鸣,也没有窈窕少女裸露的光滑如玉般的肢体,更没有消渴解暑的清凉饮料……
穿行在这坐城,满目瓦砾,满目创痍,巨大的地震波,恣意地逗弄着人类,积聚人类智慧的羌族风格的钢混建筑,瞬间被摆放成怎么都想象不到的奇形怪状的样子,平日里稳若磐石的人类赖以遮风避雨的庞大楼体,或深埋地下几十米仅仅露出薄薄的一层楼顶、或罗汉般堆叠的东倒西歪、或投掷远方眨眼南北、或四分五裂缈无踪影,苍忙世界一个小小的举动,恍若淘气孩童,不耐烦间挥手推倒的五彩积木,却让人间柔肠百断、心碎千千。
这座城,原本就是一座死城,一座流尽了人间泪水的哀城!!
穿行在北川老城区窄窄的巷街,脚下的路异常的艰难。
一顶没有警徽的警帽,沾满泥土,躺在砸扁的警车边,不知道警帽的主人是否安然无恙?是北川的勇士?还是救援的外地英雄?
一包包没有拆封散落在瓦砾里的“旺旺”米通,一筐裹满泥土稻壳的松花蛋滚落在支离破碎的家具下。一坛坛豆豉、辣酱、泡菜碎裂的东倒西歪,汁液凝固了流淌,这一定是小杂货铺的东西,杂货铺的店主逃生了么?
两条橘色的枕巾镶嵌在泥土里,白色的女士小坤包拉练锈蚀了……
不忍践踏阻挡我脚步的这些东西,更不忍把这些曾被主人悉心使用的东西踢开。
残破楼体的防盗窗阳台里,一家三口的衣物整齐地悬挂在晾衣架上,女人的镂空内衣,绿色带白杠的小学生校服,肥大的男人体恤和休闲裤,有尘土,还有些泛白,是啊,经历三个多月的风吹日晒了,洗衣服的女主人还能回来细细叠放么?绿色的校服什么时候还能佩上鲜艳的红领巾?大体恤休闲裤早该随男人携妻儿去湔水、去通达新老城区的铁索大吊桥游玩了。老天啊,您一哆嗦,把这天伦一家捉弄到哪里去了?
步伐好沉好沉,是因为颤抖的腿,颤抖的腿是因为颤抖的心。
【二】
踏入北川界,恰逢5.12汶川大地震百日祭,浓浓白白的祭祀香火,弥漫在夏日火热的空气里,供果酒水占据在北川城外每一个能祭祀的地盘和空间。
执著的来北川,不是带着猎奇,不是带着崇高的志愿,只是牵挂曾经两过北川时候带来的幸福和一定要北川行的许诺。
前年(2006年),去九寨,途中在茂县“山菜王”歇脚,领略了原汁原味的羌食后,被羌族长老几羽长翎帽和雄悍的兽皮装束震慑,随即又被俊美羌族少年一曲悠悠羌笛和用长长麦管吸啜的杂酒陶醉,回首间,羌族姐妹婀娜的舞姿、清丽的歌喉和脚上绣着祥云的美鞋,彻彻底底让我牢牢记住了这个独特、且有着悠久历史的、与中国历史文化不可切割的民族。
天军告诉我,离茂县不远还有一个地道的羌族自治县北川,那一刻,萌生了羌寨行的念头。
实现羌寨之行是在去年(2007年)8月下旬的初秋,北川西羌九皇山最美好的季节以她最俊美的姿态接纳了我,弯翘犄角的美羊门楼,金寨坊风格迥异的羌寨,记载羌族历史的尔玛古道,无不透露出羌文化的独特魅力。从盘古的蚕丛、鱼凫到智者姜子牙,从治水的大禹到修缮都江堰的李冰,一个个名垂华夏青史的人物,身体里都流淌着这个神奇民族的血脉。
我喜爱西羌绿的滴油的青山、喜爱西羌白的眩目的云朵、还喜爱羌人神奇的石头碉楼和有着美丽犄角的羊图腾,因了青山白云碉楼美羊,还因了这个民族的聪明智慧,我喜爱羌族,喜爱这个云朵上民族的文化,短短两天的羌寨生活,西羌九皇山到处都留下我沉湎地脚步、留恋地眼神,我抚摸无数的叶片却不摘取一羽,俯身捡拾数粒石子却不带走一枚,我知道这里的一叶一石、一草一木,都属于“羌”这个古老的民族。
告别羌山羌水、羌笛羌人时,从山顶羌女并不丰盛的店铺里,挑拣了一支嵌着铜环缠着红色丝线的牦牛发簪,携一箱泥坛羌酒,对着夕阳里的九黄山和无数个美羊图腾挥手。
时光如梭,北川西羌九皇山的美好,一直作为我的幸福滋味不断反刍品味,这种幸福的滋味还没有真正悟透和演化成我的文字的时候,天公却在今年5月12日一个毫无任何特色的日子里,抖擞精神,眨巴眨巴眼睛,就重创了羌人的美山美水。
曾经文静沉稳的山脉,撕裂了绿色的伪装,张开了一道道大嘴,吞没了北川,曾经柔为丝绸般的湔江(通口河)水,咆哮着扯走人类的财富……
我不知道九皇山天街坊上西羌第一塔是否安好?
图片
第一塔上敲羊皮鼓吹羌骨笛的那位憨厚的大叔是否还在?
热情调皮的羌族小伙,是否还在欢快的舞着雄悍的羌舞?
猿王洞前山壑间长长的情人桥,是否还在涧风里摆动?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那里面发生了什么。
我只知道,曾经美好的九皇山现在不再开放!
我只知道北川现在是一座被特警把守封闭的空城!
【三】
8月16日,农历鬼节第二天,又是一个下午两点,我站在了北川城外高高的山坡上,小心翼翼挪动双脚,不踩踏比比皆是的祭祀遇难者的香火,俯视残破的北川城。
跃入眼帘的是绿色湔江在废城成“U”形缓缓流过,“Z”字形灰白色的入城公路被黛色的山坡遮挡成倒“U”型,与湔江形成一个大写的“八”字,大大的“八”字在残楼瓦砾背景的衬托下,异常触目。
伸入湔江的一脉山的母峰,坍塌山体裸露出的泥土,似乎是一个女性长眠的侧面脸,而“脸”周围青色山体的局部,似一只坚硬的手爪,紧紧攥住长眠女性的脸,难道这幅自然图里预示着什么吗?
眼前低凹的城区突然变的阴霾黯然,而环城的山体却阳光灿烂,是一大片云朵飘过阻挡了阳光,笼罩了北川城,是不是苍天也羞愧了,用云朵掩饰对大地犯下的罪行?
异样的感觉袭进身体,我不寒而栗。
沿着高大铁丝网走向守城的特警,请求特警允许我开车入城,尽管车前挡风玻璃放着特别通行证和四川新闻中心采访证,特警还是用不容商量的口吻和普通话拒绝了我的要求。说话的特警身体高大魁伟,眉宇间透着北方汉子的粗犷和英武。
我挨近特警小声问他一定不是四川人,特警怔了下回答:山东泰安。我说我是江苏的,我们是邻居,挨得好近,经常去泰安爬泰山。特警面色立即缓和不少,似乎对我的话有了兴趣,旁边维持秩序的几位特警也走过来和我一起攀谈起来。
共同熟悉的地域风情拉近了我和几位特警的情感交流距离,特警告诉我,第一批赴北川执行任务的战友身体严重透支,他们是第二批换防的,来了一个多月,负责北川的封城,北川一直没有解禁,这两天是鬼节,当地人称7月半,又临近地震百日祭,因此,陆续放行一部分北川居民返城祭奠,东西只许带进,不许带出。特警还告诉我,每天都要面对悲伤的灾民,甚至情绪异常激动的灾民,承受时刻在抖动的大地,他们很累很乏,也很想家,但是,他们是人民警察,是特殊的人民警察,要投入抗震救灾工作。
值勤的特警中有位12集团军的转业军人,听说我也曾是军人,更加热情了。我感觉,在中国,只要有过军旅生涯的人,因了军装,因了军营,因了相同的军人身份,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无需更多的语言交流,便建立一种牢牢的信任。
不知不觉,和特警聊了20多分钟,突然觉得,这群铁血男儿是如此的可爱,如此的可敬,如果不是特殊的灾难现场,如果不是时间紧迫,真想和这群铮铮铁骨男子汉坐在成都茶店里大碗喝茶,好好聊聊。
彼此信任和准老乡的缘故,特警允许我们仨人随同返城祭奠的八、九个人一起进入戒严的北川城。
【四】
绕过特警身后两辆大型消毒车和穿戴防疫服装的军人,走向震后的北川城。
扑入眼帘的第一个废墟,就是掩埋了一千多名师生的北川中学,而此时此刻的北川中学,瓦砾上已经有簇簇小草在迎风轻轻摇晃,是不是在为早逝的生命舞出哀思?
通达新老城区的铁索桥荡然无存……
曾经热闹繁荣的北川大酒店,也少了两层,孤寂颓废地站立在新区,隔着湔水冷漠地注视着对岸一片平坦的泥土,泥土下几十米深处,在地震瞬间活活掩埋进上万名生命……
腐臭和香火弥漫在这座空城,这座令人窒息的城。
炎热的日头,沉重的心情,腿开始颤抖,颤抖的承不起身体的重量,蹒跚移行到一棵树下石块旁,静静地坐在北川的泥土上感受这里曾经的一切。
细细打量眼前的建筑,是联想计算机门市,门楣上“北川门户网站”兰色的字迹清晰完整,大楼窗户沿上都有弯翘犄角的美羊图腾。
远处,一名祭奠者在拆卸一辆半埋在泥土里的人力三轮车的车牌,车牌卸下后,仔细用手抹干净,放入双肩背囊向城外走去。
另一个远处,一名拄着双拐的女子,在两名男子的搀扶下趔趄着跪下,对着一堆什物久久地叩首,又在两名男子的搀扶下起身向新城区走去……
裸露在外的胳膊和腿,突然巨痒起来,用手去挠,却惊起几只几乎看不见的半个芝麻大的黑色蚊虫,用手拍打,黑蚊迅速逃离,盯咬处出现红点,突然间明白,为什么要封闭北川城。
不远处的地面,一堆黑色的人便已经风干,不知道是北川遇难者遗留的,还是救援者遗留的,几只象苍蝇的牛虻,围着那堆秽物旋转,却并没有声音,奇怪,灾难,让这座城没了声音,连灾后的蚊蝇都成了哑巴,震后的消杀力度,依然让生命力极度顽强的蚊蝇滋生。
我不得不慨而叹之:生命在这个世界有时候是那么的脆弱,有时候又是那么的顽强。
此时此刻,一个人面对残破的北川空城,看着胳膊和腿上点点红斑,呼吸突然困难起来,恐惧的感觉油然而生,全身的汗毛倒立,我觉得我的身边围满了这座城里无数的冤魂,也许,他(她、它)们并无恶意,只是诉说对亲人的思念,对阳世的不舍,对天堂的迷茫……
摸出手机,给天军打电话, 这座无人的空城,没有信号。
同行的另一位女性王姑娘不愿近距离接触悲惨境地,留在山坡上等候。
天军速度快,走前头,他要看遍多次来过的、曾经美丽的北川城,而现在饱受地震蹂躏残破的样子,留下一路叹息 。
无奈,用指甲钳拆开牛仔七分裤的裤脚,拉低裤腰,延长裤脚长度保护裸露的小腿,用丝巾包裹头面部,翻出清凉油涂抹黑蚊盯咬处。
很后悔没有买一瓶白酒洒在脚下的土地,很后悔没有买一柱香火点燃,还很后悔没有为自己穿一身长裤长衫,更后悔没有听从朋友的话,佩带一个红色的手链。后悔的事情很多,却不后悔早许下来北川的诺言,不后悔崇视羌族山水和文化的至爱。
罢罢罢,抱住肩膀,调整呼吸,站在太阳地,仰头看头顶的太阳,吸纳阳气,等侯同行天军的返回。
【五】
坚定地走遍北川城的天军,摇摇晃晃的身影,终于出现在远出一座残楼前,脸色绯红,气喘不绝,拎着相机的手抱在胸前,步态似乎也有些踉跄。
出城的路虽然还是来时路,却感到遥远,感到吃力,天军同志要帮我背包,伸手拉我一起前行,我婉拒了。我知道,他也一定并不比我好受,我能走进北川,就一定能走出北川。
又一次经过北川中学,向中学后面的坡上爬去,坡上是入北川的公路,想到一千多名师生至今依然长眠废墟下,心剧烈的疼痛起来,忽然,我大汗淋漓,心慌气短,几乎虚脱。难道是旁边废墟下,那一千多名罹难的灵魂,残留在大地中的生物电波,发出的求救信息,让我又感应到了?还是暑热蒸人的蜀地八月,在空寂无人的死城和浓烈的消杀药水味中转悠了几个小时,心情沉重,滴水未进中暑了?我停下攀爬的脚步,蹲在陡陡的羊肠小道上,一手掐住合谷和曲池,做着深呼吸,默默地祈祷,愿罹难的人们安息,在另一个世界,没有灾难,没有痛苦。歇了20分钟,症状稍有缓解,继续攀爬,天军摘过我的包,助我一臂之力,把我拽上坡,终于,看到坡上那顶蓝色伞和伞下等候我们的王姑娘。
临近封城的大门,四个山东特警反背着手,跨立姿势审视出入的人,远远地看到我,关切地询问我是不是中暑了,督促我赶紧上车开空调,好感激的一笑送给可爱的山东特警,点点头算做和他们的告别。
再回首,北川天空晴朗明净,几丝游云懒懒的飘动,城外山坡上祭祀的青烟缭绕在灌木里,用力关上车门,和空气似乎都凝固的北川城告别。
我努力抑制翻江倒海的胃腹,却抑制不住晕呼呼的头颅。车里凉嗖嗖的空调,甜丝丝的绿茶,让我有所缓解。
路边遍布的灾民防震棚前,陆陆续续挂满了金黄的玉米棒,防震蓬前的水泥地坪,也有成片的红海椒在晾晒。
铁血四十师的帐篷整齐地搭建在庄稼地里,身形瘦削面色黛黑士兵,用油漆在路边砖块大的石头上,画了五个与奥运会上一模一样的奥运福娃,还有全世界人民都熟悉的奥运五环,铁血四十师的士兵,在抗震救灾中是用生命和血汗营救北川人的,是第一个从云南开赴北川救灾的部队,此时此刻的铁血士兵,在低矮闷热的迷彩帐篷里,是否能通过电视看到正在进行的奥运赛事?
我们随车带了些图书是送给灾区小朋友的,经过当地人指点,向擂鼓镇帐篷红领巾书屋前进。擂鼓镇离北川很近,俄罗斯的米--26给唐家山堰塞湖运送挖掘机,就是从这里起飞的,上演了举世瞩目的“老鹰抓小鸡”的运送奇迹。当时临时推出的一片土地作为简易机场,现在已经长满青青茅草。
山下用碎石铺路、水泥打地坪的一片空地,是擂鼓镇新的居民点,不大的广场上树立两块石头,分别镌刻着“石破天惊人”“国泰民安”的红色字迹,兰色的救灾帐篷住人,白色的帐篷有的是帐篷信用社、帐篷商店,我们寻找的帐篷图书馆就夹杂在其中。
负责接受捐赠的人说着流利的普通话,伏在长桌上认真地登记我们带去的每一本书籍。桌子另一头,一个穿迷彩裤、黑体恤的小伙儿,轻声轻语地给几个坐在他身边的小孩说故事,我走到他的身旁,他讲话刚好告一段落,站起身朝我友好的笑笑说,谢谢你们来灾区,谢谢你们给灾区捐物。我听出小伙子是东北口音,赶紧问他,东北人怎么在这里啊?小伙子说他是长春人,5月13日就从长春出发,16日赶到擂鼓镇的,是志愿者。
将近100天,这个年轻的志愿者在这里怎么生活、干些什么、原来是否有工作、什么时候回家等一系列问题,此时此刻成了我想了解这个志愿者的最大愿望。
【六】
一百天很长,一百天也很短,快乐祥和的日子,一百天如梭如光,艰难困苦的日子,一百天应该是煎熬是隐忍吧。疑问和想法一说出,两个志愿者立即否定了。
长春志愿者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王燕欧,燕欧告诉我,他有份不错的工作,在长春某报做记者。5月12日的晚上听说汶川大地震,不顾家人和朋友的阻止,13号毅然决然辞去工作,星夜兼程赶到受灾最严重的北川。看到千疮百孔的北川,看到少爹缺母的孩童,燕欧对着瓢泼大雨中依然地摇山动的北川许下誓言:以肉身和知识,照顾灾难中的孩童,直到北川不再摇动,直到北川建好的那刻。
燕欧的目光安静而热情,语气平和却语出惊人,这个年轻小伙子言谈举止间溢出坚定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了我,尤其是眉宇间透出凛凛英气,本来就高大挺拔的身躯,在我的眼里更加完美,突然觉得燕欧是我这次北川行的点睛之处。
燕欧还告诉我,郑州的年轻人原本有一个收入不错的小店,5月13日关闭店铺,携带部分援助灾民物品,只身来到北川,一百天过去了,带来的物品早早分发完毕,只有一架黑色的长焦数码相机一刻不离地悬挂胸前。
和燕欧说话的时候,两个很小的孩子,一直蹲在书架前的地上,捧着书认真地阅读,不知道这两个孩子是否是孤儿,不敢多问,这些伤心事永远不提最好。
不想打搅孩子的阅读,蹲下来,默默地观察读书的孩子,也抽出一本书陪读:“只要我还活着,能看到这阳光,这无云的天空,我就不可能不幸福!——安妮•弗兰克” 。随手竟然抽出了著名的《安妮日记》,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少女安妮和父母被好心的德国友人隐藏在地下室,从13岁生日(1942年6月12日)写起,一直写到1944年8月4日,他们的隐居地被德国党卫军查抄,安妮全家被处死。小小的安妮虽然只享受了13个季节的阳光白云,却总结了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坚强地活着。是啊,孩子,你们能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天地不老,江水不涸,青山依旧,只有草木枯荣,生灵轮回,这一世沦为人,就要一生珍惜,珍惜生命,珍惜亲情友情,更要珍惜爱自己的人。
我从看书的孩童身边站起,燕欧又和我聊起来,燕欧和其他志愿者在北川的一百个日夜,没有吃过灾民的一口粮,没有喝过灾民的一口水,自费购买食品和水,夜里和衣而卧,少有的几件衣服由于当初参与救援而破损。此时此刻,燕欧身上穿着带有特警标志的黑色体恤和陆军迷彩裤,我想可能是救援部队官兵赠予或者借给燕欧的吧。
随着救援工作接近尾声,大批志愿者陆续返回故乡,燕欧没有离去,却深深的爱上北川,依然和北川擂鼓镇的孩子一起生活学习,参与擂鼓镇的灾后自建。帐篷里的日日夜夜,燕欧觉得很充实,没有迷茫,没有旁念。燕欧似乎很愿意和我说话,我当然更愿意和他交谈,时钟却毫不留情的提醒我必须离开北川,燕欧给我留下电话号码和QQ,燕欧和郑州小伙子把我们送出很远。
穿过擂鼓镇帐篷“街区”,车辆驶入擂鼓新修的水泥大道,远处青山和擂鼓镇到处飘扬“抗震救灾”和“以奥运精神重建家园”的旗帜,让心情振奋许多。在北川城区废墟里头晕恶心的感觉没有了,进食的欲望强烈起来。拿出沉甸甸甜蜜蜜的龙泉水蜜桃,张口噬咬间,燕欧和郑州志愿者菜色的脸庞浮现眼前,晕,怎么没有早想起呢,掉转车头,返回红领巾书屋,把又大又甜的水蜜桃放到了燕欧和郑州小伙子手里,看得出,他们很开心,车辆驶出很远,燕欧和郑州志愿者站在帐篷街区路口,举着鲜红的水蜜桃和我们告别的手,一直在摆动……
再次向大山深处的北川擂鼓镇道别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沉,余辉没有想像中的红火,天空也没有想象中的洁净,只有几丝镶了一点金边的云彩匆匆飘过,难道云朵又要飘向北川城,去羞愧地覆盖颠覆大地的罪证么?也许,这些丝丝缕缕的白云,就是生者祭祀的香火带给天堂长眠亲人的音信吧。
我挥手,百孔千疮的北川,我挥手,这座寂静的死城。
2008年8月20日于汶川大地震百日字
谨以此文:
向罹难者致哀!
向志愿者致敬!
作者简介
叶晓藜,1965年12月出生于新疆伊犁,1978年考入军校,毕业后分配到某野战医院工作,先后取得专科、本科学历。转业到地方院校后,从事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热爱读书和音乐,喜欢旅行和摄影,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遵道的年画汉旺的钟》《冷冷的中秋月》等多篇小说、散文和随笔。2014年由南京出版社出版《莺啼树杪弦》纪实散文集。
声明:本平台以原创首发为主,作者所表达的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转载或来自于网络的图片、文字,如涉及版权问题,我们将予以删除。
责任编辑:马 国
编 审:侍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