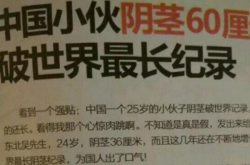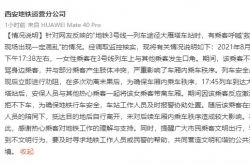发表自话题:小区里的社死现场
“那些大概都是生活不再会被衣食住行所烦恼的人思考的事,但现在,可能大多数人还是要考虑衣食住行吧。”
花家地的春天又来了。
这个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道西南部的社区,多得是老年人在单元楼门口打牌、聊天、晒太阳。租房市场也如天气回暖,花家地北里一套四五十平米的住宅,月租金可达七千元上下。
这里最早本是一片花椒地。而如今,那个叫“花椒地”的原名早已被人遗忘,这里从京郊的村庄变为了紧邻东北四环的“亚洲第二大住宅社区”。高校、购物中心、写字楼,包围着这些栋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回迁房。
但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这里还藏着另外一个世界。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北京市建立起大量人民防空工程。在花家地北里小区,每个高层住宅楼下,都建有一间高约两米的小屋——那其实是一个个洞口,通向那个被折叠起来的空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那里有理发店、裁缝铺,也是小商贩与民工的居住地;而现在,只有两个洞口仍然开放,一个是存车处,另一个是“地瓜社区”。
地瓜社区是一处共享空间,位于花家地北里西南侧的一处防空洞内。和另一处防空洞不同,这里完全是一片明亮的暖黄,洞口处的玻璃上写着“您家门口的共享艺术社区”——这是北京市三家地瓜社区的其中之一,创始人名叫周子书,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教授。
他的愿景是,用地瓜社区将闲置的地下空间打造为连接地上与地下居民的公共空间,吸引更多人来到这里,重建社区中人与人的连结。但现在,地瓜社区花家地北里店的管理员告诉全现在,这里常年都是空置的状态。
洞

地瓜社区花家地北里店入口。李一鸣 摄
周子书硕士就读的中央美术学院,与花家地北里仅一条马路之隔。但让他关注到这里地下室的,是其在英国留学时看到的一则新闻。
2012年,周子书到英国的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攻读他的第二个硕士学位:叙事性空间策划及设计。一天,他在BBC看到一则新闻,称曼彻斯特政府准备在地下建一个超市,挖掘中,发现了维多利亚时代一个住过人的地下室。他继而了解到,即便在当今的美国纽约,也有很多人住在地下。
周子书由此想到,在北京,同样有大量外来人口,因为通勤时间与经济方面的原因,选择住在中心城区的防空地下室中。当时,他就定下了自己毕业设计的主题——研究北京地下室的城市外来移民。
根据《京华时报》《北京晚报》等媒体梳理,上世纪80年代开始,北京结合地面建筑建了大量的地下人防工程,但很多被闲置。因缺少专项基金维护和专人管理,许多地下人防工程日渐破败。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地下空间被利用起来。到2004年,北京形成了人防工程出租的高峰,并逐年递增。
地下室涌入的大量居民造成了地上地下居民们激烈的矛盾,安全事故频发。
2005年,北京正式实施《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办法》,详细规定了地下空间的安全标准与使用规范。但据《京华时报》等媒体2011年报道,该办法五年来“收效甚微”。2010年底,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出台《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并于次年2月实施,规定地下储藏室一律不得出租供人居住。2010年12月6日,时任北京市民防局局长王永新表示,从2011年上半年开始,将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对人防工程中的散居户进行清退。
但更加严格的政策迅速遭遇了反弹。据《中国经济周刊》《财经》等媒体报道,2010年12月底,曾有地下室承租人在收到要求他们清理租户的消息后,于次日在朝阳公园门口聚集,人数达到数百人。2012年8月,《北京青年报》报道称,自《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实施一年多以来,地下空间管理混乱的状况并未因此改变,地下人口反而在不断增多,地上与地下居民的矛盾日益凸显,甚至会有小区业主将管理部门告上法庭。
在2015年的一场演讲中,周子书称,之所以选择在2013年启动地下室设计项目,就是因为在当时“看到了政府政策在治理地下室方面的无能为力”。
2013年,周子书回到北京,希望能凭借自己的能力改变地下室的管理与使用状况。作为一名设计师,他的想法并不是单纯地进行地下空间的改造,而是“重新定义”地下空间,让居住在地下室中的人们被赋予“鼠族”(指常年居住于地下室,不见天日的“北漂”)之外新的角色,获得“空间正义”。
“我们的工作不只是装修这些地下室,让它们看上去漂漂亮亮的,”周子书2016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实际上它关乎改善居民的生活,营造一种新的社区感。我们想要利用这些私人空间,让它们再次成为公共空间。”
周子书进行毕业设计调研的地方就是花家地北里。望京地区曾是一片乡村,建成于1994年的花家地北里有三栋居民楼中的居民都是原望京地区的农民,如今会坐在单元楼门口聊天的几位老人,原来也都来自同一个生产队。社区的空地上,还摆着闲置的沙发与桌椅。
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生罗森也曾经在本科期间对花家地的社区展开过为期四年的田野调查,他于2019年出版的《花家地2014-2017》一书,记录了这片社区二十余年的成长史。整个望京地区在八九十年代以前是一片农村,曾经住在望京陈家屯,现在家住花家地北里的陈国兴(化名)称,自己以前在村里的生产队干活,负责把村里种植的农产品拉车运往西直门粮库。“现在脚底下的就是我们村。”在村里时,曾经的村民们习惯于三五成群聚在村里路口处聊天,现在,他们搬到了单元楼门口。
而这些住进单元楼的农民,在社区中也仍然保持着原有的生活习惯,将空地拾掇成菜园。此前接受采访时,罗森提到,“这些楼是政府按照一种当时统一的社区模式统一盖的。这导致了它现实的居住状况与小区原本的规划非常不匹配的局面,很多人会把几个户型之间的墙打穿,再分成隔间,后来流动人口多了,很多人会住在这里的地下室。”
这片在田地上建成的社区仍保持着野蛮生长而具有生命力的社会网络,地下空间也同样如此,在这里,外来者可以被轻松地识别出来。
周子书就是那个外来者。在英国时,他的设想是把一间地下室改造成一个全球图书馆,向全世界的每个图书馆募集一本书,让地下室的居民“感受到来自全世界的关爱”。当时,他还和大英博物馆谈好了合作,对方也很乐于帮助实现他的设想。
但来到花家地北里,周子书发现,就在地下室入口旁边就摆放着一座“朝阳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那是一台两米多高的机器,读者可以通过它完成机器中图书的自动借还。他在旁边呆了一天,发现白天这里的来访者寥寥;倒是晚上有人陆续光顾——他们把这儿当成了公共厕所。
从中央美院毕业后,周子书在中国美术馆担任过设计总监和建筑策展人。当时的一件小事让他印象深刻:从2011年开始,中国美术馆免费向公众开放。而就在免费开放的第一天,一位附近的街坊大妈买完菜后,直接进入美术馆利用厕所里的自来水洗菜。周子书认为,老人的行为是因为老旧小区缺乏基础设施下的不得已之举。他意识到,设计在艺术追求之外,更需要被运用到迫切的需求之中。
那地下室居民们真实的需求是什么呢?2013年,周子书走进了防空洞,他想寻找一个答案。
交换

第一次“技能交换”。图源网络
串连起地下室的是一条狭长的走廊,光线昏暗,分支走廊上晾满衣服,通向一间间小屋。40个住户共用两个厕所,还有刷卡收费的淋浴间。有的墙上刻着字:“不管多困难,距离多遥远,我都不会放手”。周子书戴黑框眼镜,蓄着长发,刚进地下室时,这里的居民都以为他是记者。
周子书找到地下室的房东,表示想租住个房间,做一个“艺术项目”。虽然小区就在中央美院隔壁,但房东第一次听说“艺术项目”这种东西。周子书和房东谈了两个小时,但对方仍然困惑,没有同意租给他。
没过多久,周子书再次来到这里。这次,房东的门口多了一块地毯。他告诉周子书,上次谈话过后,他想了很多,也跟妻女聊了一下。他觉得,他现在30岁了,可能需要“改变一些”。于是,周子书租到了房东平时用来打游戏的房间。
在地下室拥有了一席之地,也通过房东介绍认识了其他地下居民,但获取信任还需要时间。周子书开始在走廊里扫地,给地下室做卫生,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观察地下室的一些细小变化:
他通过房间门口的拖鞋数量注意到,每个三到五平米的小屋会住一到两个人。
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两个人。一位是奥迪的汽修工,他和周子书说,“现在的人特别无聊,只知道房子、车子和女人。”而他想学新能源技术。还有一位是锅炉工,他听说做平面设计特别赚钱,于是让父亲掏了9100元资助他去学了三个月的Photoshop,学完之后,却因为找不到人介绍工作,还是做回了锅炉工。为此,他专门写了一封信,叫做《人生两大陷阱》,一是和别人作比较,二就是证明自己。
周子书发现,地下室里90%的年轻人身上展现出的活力和求知欲,比“地上”的年轻人都强。他们缺乏的,只是一些交流的机会与来自地上的指引。
周子书成功加入了地下居民们的日常聚餐。在交流中,周子书意识到,他们所需要的,并不是将地下室的物质条件改造得多么好,而是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的可能。他产生了一个新想法——技能交换,让分别居住在地上与地下的人进行对话,帮助后者了解一些职业发展的可能。
第一次技能交换发生在一张被一分两半的床上。来自地上的一方是32岁的软件工程师,他拥有心理学背景,希望将心理治疗与理疗结合在一起;地下一方则是一位25岁的足疗师,他很想学软件工程。他们先是面对而坐,交流计算机知识;然后再将床合而为一,进行理疗的现场教学。
第一次试验获得成功,双方都觉得这种形式非常有趣。房东也参与了技能交换。周子书为他介绍来了一位女生。在她的苹果电脑上,房东学到了开设淘宝店和销售商品的全过程。作为回报,他为对方唱了一首《我的歌声里》。
有了个还算不错的开头,周子书开始启动他更多的改造计划。
他粉刷了这间用于技能交换的房间。一开始,他想把墙壁刷成全白,但一个居民对他说:“能不能不要全刷白?我们赚了钱就想回家去盖个房子,你能不能把这里刷成一个房子的形状?”于是,周子书将墙体的下半部分刷成白色,又在一面墙上画了个白色的“屋顶”。在地下室的入口处,他设置了一个小机关——在“地下室招租”这个招牌中的“下”字背后装一个小马达,按下开关,T字形会旋转起来,一会是“下”,一会是“上”。
线

旋转的“地下室”。图源网络
接下来,周子书想改变地下室的“地下”色彩。
这座防空洞有八行四列,由一条主走廊贯穿。他在整个空间的入口处涂上一个大大的“G”,在其后涂下“12345678”。每条横向的走廊都改成了楼层,这间平面的地下小城被“立了起来”。走廊的颜色也被重新涂饰。原先被用于备战的防空洞的门框比较宽,周子书团队将门后的前后两面刷上不同颜色的油漆,这样,居民们回家时看到的是温暖的黄色,离开后则是代表希望的蓝色。
在另一个房间,周子书计划着帮助更多来自地上地下的年轻人完成技能交换的组队。他在两面相对的墙上分别绘制了巨幅的中国地图,天花板上垂下几十条五颜六色的线。一根线分成两头,一个人拉起一种颜色绳子的一头,固定在一侧墙上自己家乡的位置,在旁边写下自己交换的技能和故事;另一个人可以在墙上寻找自己想学习的技能,拉着那只绳子的另一头,固定在另一面墙上。
这样,一个房间里,可以完成几十位组技能交换。地上与地下,通过一根根线,在这个空间里实现了连结。
而周子书的计划并不仅仅是一个房间。他想实现的,是将地下空间进行整体改造,实现地上与地下的和谐共生。在他毕业作品的设计图中,整个防空地下室被分为四个部分,上部出租给艺术家与设计师;下部出租给新生代农民工;尽头是社区居民的公共空间;中间则是实现技能交换的教室。
根据自己过往成功的实验,周子书相信北京的防空地下室可以在未来被转化为连接农村和城市的中转平台。他计划着这里可以举办“每年三次,每次三个月”的“都市工作坊”——租赁地下室作为工作室的艺术从业者们,需要每周为住在这里的年轻农民工们免费上两次课;参加这个都市工作坊的农民工学员们,也必须为设计师和艺术家们做助手。
2014年6月,凭借这份名为《重新赋权——北京防空地下室的转变》的毕业设计,周子书成为了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十年来第一位得A的中国毕业生。当年九月,一篇名为《让北漂生活更有尊严,设计师暴改央美附近地下室!》的微信公众号文章记录了他的毕业设计,包括改造地下空间的全过程,在当时刷爆了朋友圈,转发数在几天内达到了十几万。
论文中期答辩时,这部毕业设计曾被部分老师们质疑,其中重要一点就是项目资金来源的问题。为了进行商业化改造,周子书在网上进行了一场调研,收集网友们对于地下室改造的想法。在调研中,周子书发现,很多年轻人毕业想创业,但无力支付高昂的工作室租金。而地下空间,月租金少至600,多至2000,一方面为地上的年轻人提供了价格低廉的创业工作室,另一方面也能供给改造,还能补贴农民工弱势群体的住宿费用——现在,地瓜社区甘露西园店还有一半供创业团队租用,一间工作室月租金为两三千元。
随着这个项目被大众所知晓,周子书也迅速被各种信息淹没。几家大型房企找到他,希望能合作设计并进行投资,还有著名连锁店希望入驻。房东告诉他,来到地下室的人突然多了起来。
2014年底,很多人在微博上给周子书留言。其中一个,是时任亚运村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的韩酉晨。他说,在安苑北里社区,有一个560平米的防空洞,长期闲置,希望能够与周子书的团队合作,政府负责基础设施改造,周子书团队负责设计与运营。
双方一拍即合。
2015年二月,北京地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吸纳了来自包括企业家冯仑在内的七十余万元资金。周子书的团队有机会将那个未完成的愿景实现出来,它的名字叫“地瓜社区”。
断裂

地瓜社区甘露西园店入口。李一鸣 摄
“地瓜”这个名字来自于周子书2003年刚刚来到北京时所经历的场景。
当时,他从江苏老家坐着绿皮车来到北京上学。一位朋友穿着军大衣来车站接他,两人见面,对方从怀里掏出个烤地瓜,一掰两半,一人一半吃了起来。
这个分享的场面,一直印在他的脑子里。两块地瓜,一块分给当地人,一块分给外来者。周子书原初的设计,正是计划让地上与地下居民实现连接与分享。但当团队正式进入安苑北里的这间防空地下室的时候,那里早已空无一人。
据《人民日报》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2009年国庆60周年期间,防空地下室曾被关停过几个月。2011年开始,防空地下室开始实行全面整治。北京市政府在2010年年底称,要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对人防工程的散居户进行清退,从此全市的人防工程一律不得住人。
2015年之前,这处位于安苑北里19号楼的地下室一直是出租小旅馆。2014年底,地下室被收回了街道手中。但新的问题随之到来:《北京晚报》曾报道,地下室渗水严重,有人居住时,地下居民尚会维修;而人们离开后,积水深度能达到二十公分。
在今天的地瓜社区安苑北里店,依然能看到开业之初,居民们活动的照片。
一名社区管理员告诉全现在,在地瓜社区正式运营的前两年时间,这里会有年轻人前来组织讨论会、观影会等活动,而近两年,来到这里的大多都是老年人与他们的孙辈。空间中的讨论室与放映厅,长期处于空置状态。社区的运营人员也从原来的十人左右减少到现在的两人。地下室被分为免费区和付费区。目前,这里的盈利来源主要是将付费空间租出去,有人在这里开设书法、绘画等兴趣班,也有社区乐队来此排练。
2019年7月,地瓜社区花家地北里店也正式开始运营。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街道负责人表示,要将这里打造为一个“高级的艺术空间”。这里的管理员告诉全现在,由于下楼不便,小区里的老年人极少会来到这里。受到从去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影响,社区数次关停,直到今年3月才正式获准开门营业。谈及地瓜社区的原初设想,管理员觉得那太过“理想化”——这个450平米的防空地下室,长期都是他一个人在此守候。
地瓜社区甘露西园店管理员则告诉全现在,地瓜社区基本上可以说是社区的服务空间,而消防、人防、街道都是其监管部门,会定期前检查。在举办活动上,也能感受到不少“拘束”,比如为防止人员聚集,会对人数有着严格的限制。“挺好的,干不了违法乱纪的事了。”这位管理员表示。通向地下室的楼梯较陡——高约20公分——加上阴暗见不到阳光,老年人会对地下室较为忌惮,因此,来到地瓜社区的居民并不算多。
《北京日报》于2018年5月的调查显示,在经历了2012年至2018年的全面整治腾退后,北京市地下空间许多都被改造为社区活动中心、居民议事厅、科普宣教等公益性场所。而这些公益设施大多都是政府牵头打造,其建造和维护成本都较高,而利用率却较为有限。地瓜社区则是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运营,客流较少,店员称“社区组织活动时会来一些人”。
目前,周子书团队又将地瓜社区“搬”到了成都——成都地瓜社区建在拆迁改造过后的曹家巷,完全位于地上。除了从地下改到了地上,这座“地瓜”也不再是“第三方社会组织”,而是是周子书团队受到成都市金牛区政府邀请,为曹家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设计并建立的。
在周子书的设想中,社区应该能够让“艺术和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形成新的碰撞”,但艺术与普通人之间仍然存在距离。
在周子书与罗森调研的花家地北里,虽然经历了几轮违建整治与地下室清退,这里的小吃摊、水果店、小卖部都已搬离,美院学生们的“生活区”不再,但社区依然在野蛮生长。作为花家地北里最早的住户,陈国兴(化名)告诉全现在,相比于地瓜社区,他更习惯于坐在单元楼门口,和原先生产队的工友们聊起几十年来的经历以及各家的家常。至于艺术,他认为这和他的联系仅限于,那些学生会租他的房。
地瓜社区甘露西园店管理员已经在这个空间工作了近三年,谈起地瓜社区的设想与现实,他个人觉得,地瓜社区所寄托的理想“有些超前”:“那些大概都是生活不再会被衣食住行所烦恼的人思考的事,但现在,可能大多数人还是要考虑衣食住行吧。”

花家地北里社区居民自行搭建的“凉亭”。李一鸣 摄
标签组:[地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