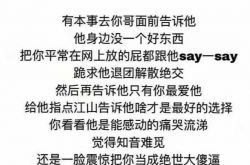发表自话题:人生就像泡沫
原标题:“姐姐”们的独立:一个精致而虚妄的理想生活“泡沫”
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的爆红,引发人们对中年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荧幕上的“姐姐”们虽然年逾三十,且大多已嫁为人妻,有的甚至经历过多次婚姻,并生儿育女,却依然如“妙龄少女”般保持着姣好的面容和身材,朝气蓬勃,才艺出众,显示出成熟女性特有的魅力。
舞台上青春洋溢的“姐姐”,似乎真的摆脱了年龄和性别的限制,释放着自己的光芒,追求着无限的可能性。她们树立起“三十岁以后”女性的理想生活范本,理所当然地成为众多女观众膜拜的对象。
同样用娱乐资本包装出来的明星真人秀节目,如《妻子的浪漫旅行》《婆婆和妈妈》等,都在关注中年女明星的生活状态。然而,对普通女性而言,女明星们精致华丽的生活,究竟能有多大的示范意义呢?成为家庭主妇的现代知识女性,她们甘愿浪费自身才华,受困于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吗?当主妇承担着无法被量化的家务劳动,她们又如何忍受自我价值得不到承认的痛苦?当一个女性在“独立自主的女性”和“可爱的讨好丈夫的妻子”之间犹疑,进而走进婚姻的“舒适牢笼”,又该如何理解她们的退缩呢?
本文从几部关于成年女性生活的小说和社会学著作出发,试图揭开真实的现代中年女性的生活,表面上她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却仍然无可奈何地堕入现实生活之网,无法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按照自己的理想方式去生活。
荧幕上独立自强、风光无限的明星“姐姐”们,或许只是提供了一个精致而虚妄的理想生活“泡沫”,普通女性可望而难以企及。具备“出走”的能力,却依然受到家庭与社会伦理无形的羁绊,这或许是现代女性特有的精神困境。
撰文 | 汤明明
最近热播的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将三十位女明星打造成逆龄生长、光彩夺目的“姐姐”,似乎在为这个时代的中年女性正名。
节目精准地戳中了现代女性的痛点,现代女性向往的是,当人生走到中年,依旧可以面容姣好、身材管理得当、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那些逐渐发胖、身材走形,活动范围仅限于菜市场、厨房和美容院的主妇们,则被嗤之以鼻。然而,真实的主妇生活似乎总是局限于家庭,总是在买菜、煮饭、洗衣服、养育孩子的“小事”上纠结,沉迷于超市购物券和街道八卦。她们似乎在选择成为主妇的那一刻,就上交了生活的可能性,只能在周而复始的生活中老去,难以“乘风破浪”。主妇为家庭付出的努力、与社会脱节的焦虑,总是被隐藏在“不够独立”的标签下。

《乘风破浪的姐姐》中光彩照人的女明星们。
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的主妇都是带着对婚姻的浪漫想象,浑然不觉地走向“舒适的牢笼”,她们更非毫无波澜地接受了这一切,并乐在其中。事实上,只要你撕开主妇生活的一角,就可以看到她们在自我意义丧失时感受到的崩裂。
在马来西亚作家黎紫书的短篇小说《烟花季节》中,主妇笑津在嫁给丈夫前,就明白了自己终将会成为被预言的棋子,回到相夫教子的人伦之中;在台湾作家黄国峻的短篇小说《归宁》里,安妮在婚前就感受到与丈夫关系的不对等,觉得结婚仿佛是为了报仇宣泄;在日本作家斋藤茂男的《饱食穷民》里,奈美子在婚前就感受到未婚夫对女性的傲慢态度,并在新婚当夜一口气吃掉了两人份的料理,再通过呕吐排解内心的焦虑。
她们称不上勇敢,甚至有一丝懦弱,表面上她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拒绝这种生活方式的可能,但都选择蜷缩在悠闲的生活内,是“独立女性”避而不及的类型,但正是这些细微琐碎的细节,暴露了主妇生活幽微隐蔽的一面,以及现代女性割裂的生存状态。

《乘风破浪的姐姐》中的表演者蓝盈莹。
被预言的棋子:“出走”前就预料到“回家的意愿”
作家如何描写中年女性的失落和缺乏突破生活的勇气?在黎紫书的小说集《此时此地》里,坐在冰室里的陌生男女互相打量,想象彼此的人生。男人觉得女人相貌平庸,原先的婴儿肥在时间的碾压下,“坐成了一座塌掉后套上几个旧轮胎的老沙发”。男人几乎可以想象出这个“长得像老姑婆”的女人,总是在反反复复瘦过身后反弹,有着“被肥胖纹淹没的皮肉”,穿“夜市场买来的容易脱色和失去弹性的廉价衣裙”。“你看看你”,在男人的注视下,女人的衰老和贫乏暴露得过于明显,以至于女人只慌乱地盯着杯子里的冰块,躲避男人的视线。
男人想要将这个天天与他在冰室里碰面的,“四十二岁还没嫁出去的女人”称为云英,想象她就是那个在凌晨三点拨通撒玛丽雅热线和自己说话的Winnie。这样的女人总是以这样的名字在深夜打电话,排遣内心的孤独。她们哭诉自己在中年时期被丈夫抛弃,或抱怨自己尚在叛逆期的儿子,或幻想一直搭载她的计程车司机有一天会向她求爱。虽然整个故事都以彼此的想象展开,但是名字和身份的不确定性,似乎也代表了日常生活中隐藏着很多像云英一样的女人。
黎紫书的另一篇小说《烟花季节》,则讲述了一个主妇“出走”的故事。笑津曾赴欧洲留学,有过一段美好但无疾而终的恋爱,回到马来西亚后嫁给了从事会计的丈夫,成为全职主妇,而她少年时代的情人安德鲁回国后成为议员。某一天,笑津在电视上看到安德鲁,想起了他提议举办的烟火大会,于是留下“想去看烟花,今晚不回来了”的字条,并故意制造手机落下的假象,以此逃避丈夫的追问。

《野菩萨》,[马来西亚]黎紫书著,新星出版社,2013年3月。
就像是许多表面上“没有故事”的主妇一样,日常生活已经消磨了笑津主动讲述的欲望,因为“平常日子,终究无事可记,也不会有一出老套的电影等着她去演,等她在弥留时掏出一堆证物,向一个年轻女生诉说一段年轻时轰轰烈烈却不堪回首的情事。”如果不是女儿无意间的询问,她仍旧会守着秘密,独自在不断地被岁月淘汰的记忆里回忆,弥补日常生活中缺失的爱情。
当丈夫总是津津乐道地重复自己特地买了头等舱的机票陪妻子生产的往事时,笑津从不领情,因为她觉得爱靠的不是计算。乏善可陈的日常生活和缱绻潮湿的少女记忆相交叉,愈发突出中年婚姻生活的脆弱与不堪。夜晚情欲涌动,笑津会“耻于摇醒枕边的丈夫,便稍侧身,在自己与丈夫的身体之间拉开一道沟壑”,开始自慰,其间留心到窗外的口琴声,沉浸在旧时的回忆中,仿佛自己仍是年轻时的肉身,躺在海绵蛋糕一样松软的床上。
事实上,笑津对丈夫的疏离和隔阂,更像是对自己命运的不满。她就是被预言了的棋子那样,嫁给步步为营的早早规划好自己人生的丈夫。而“她早知道自己终将会回到这种人伦中,相夫教子,看似圆满无瑕。每年老同学聚会时,她分外感觉到大家都各自陷进了类似的人伦里,女同学们尤其如此,像套了一个看不见的枷,而她却看见了,圆形,美丽的图案;天地,黑白,阴阳两仪,看似圆融却无法逾越。”
令人唏嘘的是,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在觉醒前,并不明白自己只是丈夫的所属品,笑津却早就知道这样的命运,并明白彻底出走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宁愿退回自己安全的笼子。她的“出走”并非是再续前缘,更没有摆脱“棋子”身份的决心,如果说爱丽丝·门罗的《逃离》中,那个试图摆脱丈夫控制、想要靠出走获得独立又无功而返的主妇还有一丝天真的莽撞,笑津甚至已经“理智”地预料到自己“回家的意愿”,和“自己对这意愿的顺从”,因此她“便疑惑着这不像出走,而像一次无从说起的赴约”。
笑津所反复回忆的爱情,也只能是弥补得不到满足的婚姻生活的致幻剂,以此实现日常生活的短暂逃离。然而黎紫书依旧平静地写着笑津的“懦弱”和叛逆的限度,但这也抛出了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为什么笑津渴望的生活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呢?

《妻子的浪漫旅行》剧照。节目中的女明星,虽人到中年,却依旧风光无限。
从“出走”到“回家”:主妇的劳动真的没有价值吗?
台湾作家黄国峻的短篇小说《归宁》里的主妇安妮,也一样困居在表面悠闲的生活里,她虽然觉得身为主妇低人一等,对自己的身份充满了厌弃感,却拼命压制自己对“更好的生活”的渴望,因为“谁有高标准,谁就发疯”。
安妮回到母亲家休产假,虽然她短暂地觉得自己再度变回了“小女孩”,却无法真正地从“妻子”和“母亲”角色中抽离,有关“主妇”的价值和意义一直撕扯着她。当她进入属于主妇的空间——菜场和厨房,就情不自禁地将自己从事的内容和丈夫的职业做比较,觉得一切都证明了主妇“低人一等”的论调。因为丈夫谈的是投资案,自己想的却是“橙子一斤多少算贵”。安妮将自己和菜场上其他的妇人并为一类,设想她们的丈夫同样“身居要职”,做的事情远比提水果回家重要。她们消失了将无损于人群,丈夫们的消失则会打断投资计划,让员工失业,引发金融动荡。
安妮的母亲和姑妈却相对接受了“低人一等”的主妇生活,并乐于向安妮传递安于现状的心得——靠光顾美容院打发时间,热衷于分享超市购物券,用闲扯和笑声驱散无聊。但安妮却觉得自己像是在牢狱中听老囚犯分享自己的经验,难以认同这种生活。在她看来,丈夫所在的“屋外”的世界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家庭生活却是凝滞的,难以与外界接轨。因此“她必须要出去屋外,看看外头是在革命或是太平,这屋内并没有可供判断其年代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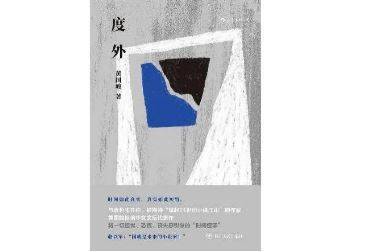
《度外》,黄国峻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
然而,当安妮试图来到象征着“外界”的图书馆,却更加深了内心的失落。虽然她并不反感育儿和烹饪有关的书籍,却猛然发现自己和一些老年人坐在一起,研究泡芙的做法。精致到华而不实的天鹅颈形状的泡芙,似乎是主妇生活的讽刺——所有的价值都放在了没有必要的事情上——因为按照丈夫的说法,“吃是低等的感官”。
因此,安妮从图书馆回来的路上遇到疯妇就极具象征意味。安妮的姑妈不明白人为什么会因为一些小事发疯,并将疯妇伤人视作治安差引发的骚乱,但安妮却将这场骚乱看作积攒已久的矛盾爆发的结果。发疯前的女人或许曾经受到严重的伤害,当时她也可能就在做有着天鹅颈的泡芙。泡芙就象征着没有意义感的、不被重视的低等生活。在这个意义上,疯妇如同安妮内心的投射,随时都可能濒临崩溃。可悲的是,安妮已经预料到即使发疯,她的痛苦也不能被理解和同情。因为那些“不必学做泡芙的人”(像丈夫一样的人)不能像主妇自身那样强烈地感受到意义的丧失和内在的崩裂,“至于算不算伤害,那就得看人的幽默感够不够了。”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指出,“家务劳动”(domestic-labor)是将“市场”与“家庭”的相互依存关系中连接起来的缺失的一环(missing-link),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并没有将“家务劳动”完全“商品化”。虽然家政服务的出现让“家务”逐渐市场化,但是如果买橙子、洗衣服等家务不由家政人员完成,而是安妮完成承担,那么这种劳动将不能产生“价值”,是“非生产性劳动”。虽然安妮也尝试赋予这种生活价值,她心想如果自己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就会拥有一个可独处的办公室,就能和丈夫一样,看着“窗外提着菜篮候车的人叹息”,但如果这样的话,“要换谁去买她家的菜呢?”

反映现代女性成长艰难历程的韩国影片《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然而,如上野千鹤子所说,当主妇付出“有用且必不可少”的劳动,却得不到法律和经济层面的补偿。遗憾的是,尽管安妮无法真正说服自己接受主妇的价值,但也无法突破现有的悠闲的生活,她对命运的态度比笑津还要消极,后者至少在有限度的范围内给自己制造了短暂逃离的机会,安妮却毫无逃离的打算,她只是不断产生幻象,觉得自己像潜水艇航行在重重景象中,随时都有可能与疯妇的命运重叠。
故事以安妮坐上车回“娘家”开头,又以坐车回丈夫所在的家结束。因此《归宁》不仅写的是回“娘家”,还有回到自己所属的主妇身份中去。那些因为自我价值不断被降格,得不到承认的痛苦和内心的骚乱,以安妮在归家途中的呼呼大睡作结。我们也无法判断这种熟睡是否也是对自我的一种催眠,以及安妮会走向怎样一种结局。
用呕吐排解焦虑:撕裂的主妇该向何处去
日本著名记者斋藤茂男的《饱食穷民》,则记录了在“厌女症”严重的日本社会,主妇对自身意义丧失和被社会遗弃的痛苦。“早上我送他(丈夫)出门后,就会被强烈的空虚感所包围。我刚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下雪的季节。我从十八楼的窗户往外望下去,外面是白茫茫的一片。我感觉全世界都抛弃了我,心里堵得难受,每天周围都只有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奈美子在接受斋藤茂男的采访时说道。
奈美子从小学习成绩优异,但因为高考失利没能读到心目中最理想的学校,与想当学者的梦想渐行渐远。毕业后,她嫁给了事业有成的淳一成为主妇。然而,奈美子并没有像笑津一样接受自己的宿命,她始终在是成为“有工作、能自立”的女人和“讨丈夫喜欢”“可爱苗条”的妻子之间犹疑。然而丈夫对奈美子的内心世界毫不关心,只有在谈及国际经济和自身的业绩时才会滔滔不绝——这一点也与《归宁》里“身居要职”的安妮的丈夫如出一辙,都将妻子作为自己的陪衬,却又因为主妇不能创造价值,内心里看不起她们。
生活的撕裂感,让奈美子变成了一个伪装的“娇妻”并患上了拒食症,靠不断拒绝食物再吐掉它们解决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好让自己贴合丈夫心目中完美的妻子形象。“吐过之后,就觉得整个世界突然变得宽敞了。心里的不安顿时烟消云散了。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之后,就会觉得,只要能够重复这个过程,就能没有任何压力地过上一整天,也不会再双眼无神地盯着他的侧脸发呆,感觉自己这样就能跟他顺利地相处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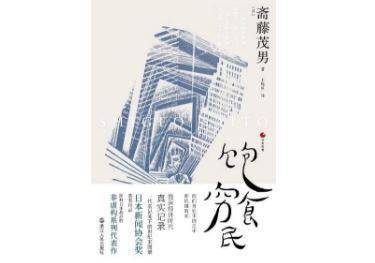
《饱食穷民》,[日]斋藤茂男著,王晓夏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
然而,这种饮鸩止渴的方法当然不能弥补奈美子内心的失落,转而通过偷情排遣内心的郁结,直到跟随丈夫回国才被迫中止。虽然奈美子在拒食症逐渐加剧后终于离开了丈夫,开始独自生活,但现实生活对奈美子来说依旧一筹莫展。斋藤茂男指出,很多像奈美子一样患有拒食症的女性就像是“煤矿里的金丝雀”,“她们就像金丝雀一样对时代和社会病态环境敏感地做出了反应,向所有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女人发出了警告。”
在笑津、安妮和奈美子身上,我们或许都可以找到一丝共性,她们曾经都学有所成,但都嫁给了事业有成、却对女性缺乏尊重的丈夫,在婚姻生活中丧失了自我的价值,时刻承受着内在崩裂带来的痛苦。然而,这可以简单地归咎为这类女性的自作自受、没有更坚决做“出走的女性”吗?

真人秀节目《婆婆和妈妈》中的林志颖与陈若仪夫妇。节目中的女明星虽然生活精致、家庭和睦,却也同样需要面对来自家庭和事业的双重压力。
事实上,“不被任何人定义”“坚持做自己”依旧是少数女性的特权。《新京报书评周刊》曾刊文(《衣食无忧之后,如何摆脱“新穷人”的窘境》)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就陆续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女性逐渐从“私领域”走向“公领域”,有了更多选择的机会,但是,“大部分的女性仍旧受到传统父权制结构下的暴力统治”,女性依旧生存在巨大的割裂中。一方面,观众可以看着《乘风破浪的姐姐》里女明星如何诠释“年龄只是一个数字”,认为自己不该被性别身份限制,现实生活中的普通的女性,却依旧在铺天盖地的化妆品广告和医美整容中挣扎。
虽然表面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我们所看到的广告也开始强调女性的独立与审美的多元,但它传递出来的对女性的关怀,只不过是一种“女性主义热”下的漂亮包装,只是娱乐资本和消费主义合谋下对“女性独立”、“女性可以勇敢做自己”话语的巧妙利用,一种不得罪任何人的、有限度的宣传策略。社会的整体氛围依旧释放了这样的信号,女性只有足够的“好看”、“有钱”、“有人爱”,才能获得幸福。
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关于“女性解放”的呼声越来越高,现代的女性往往也受过良好的教育,被鼓励走向社会实现独立,但她们仍旧会被灌输传统的为人妻、为人母的观念,依旧会陷入无爱的惶恐。就像斋藤茂男指出的那样,对于生存方式的苦恼依旧潜伏在现代女性内心深处。“自立和依存,很多女性无法掌控好二者的平衡,背负着被二者无情撕裂的宿命,踏上寻找‘自我理想’的旅途。”
作者 | 汤明明
编辑 | 徐伟 罗东
校对 | 张彦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标签组:[安妮]
上一篇:对话熊丙奇、黄灯:“二本学生”标签是我们对教育的作茧自缚 -ZAKER新闻
下一篇:自恋的人,生活在自我膨胀的泡沫里